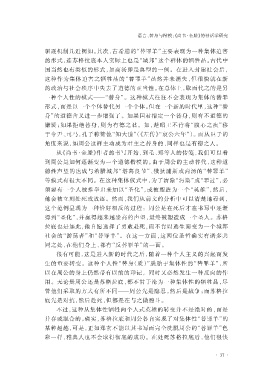Page 44 - 《社会》2021年第1期
P. 44
语言、替身与楷模:《尚书·金縢》的神话学研究
驱逐机制几近阙如。其次,古希腊的“替罪羊”主要表现为一种集体迫害
的形式,连苏格拉底本人实际上也是“城邦”这个群体的牺牲品。古代中
国当然也有类似的形式,如商汤即是典型的一例。 在进入封建社会后,
这种作为集体迫害之牺牲品的“替罪羊”虽然并未消失,但很快就在新
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中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 在总体上,取而代之的是另
—“替身”。 这种模式往往不会表现为集体的替罪
一种个人性的模式——
形式,而是以一个个体替代另一个个体。但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这种“替
身”的道德含义进一步增强了。 如果国君指定一个替身,则有不道德的
嫌疑;如果拒绝替身,则为有德之君。 如,楚昭王不肯将“腹心之疾”移
于令尹、司马,孔子称赞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 而从臣子的
角度来说,如周公这样主动成为君主之替身的,同样也是有德之人。
从《尚书·金縢》作者的书写开始,到毛、郑等人的传笺,我们可以看
到周公是如何逐渐变为一个道德楷模的。 由于周公的主动替代,这种道
德性声望的达成与希腊城邦“塔葛良节”、俄狄浦斯或商汤的“替罪羊”
等模式有很大不同。 在这种集体仪式中,为了清除“污染”或“罪过”,必
须要有一个人被推举出来加以“圣化”,或被塑造为一个“英雄”,然后,
他会被立刻处死或放逐。 然而,我们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范例呈现为一种恰好相反的过程: 周公是在死后才在书写中逐渐
得到“圣化”,并赢得越来越崇高的声望,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圣人。 苏格
拉底也是如此,他自愿选择了勇敢赴死,而不肯以逃生而变为一个城邦
社会的“ 游荡者”和“替罪羊”。 在这一方面,这两位圣哲确实有诸多共
同之处,在他们身上,都有“反替罪羊”的一面。
很有可能,这是进入新的时代之后,随着一种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发
生的重要转变。 这种个人性“替身(质)”脱胎于集体性的“替罪羊”,所
以在周公的身上仍然带有以前的印记, 同时又必然发生一种反向的作
用。 无论是周公还是苏格拉底,都不甘于沦为一种集体性的牺牲品,尽
管他们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周公先是隐忍,然后是战争;而苏格拉
底先是对抗,然后赴死,但都是在与之做缠斗。
不过,这种从集体性牺牲向个人式英雄的转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
并存或混合的。确实,苏格拉底和周公各自实现了对集体性“替罪羊”的
某种超越,可是,正如郑玄不能以其书写而完全洗脱周公的“替罪羊”色
彩一样,雅典人也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 在处死苏格拉底后,他们很快
·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