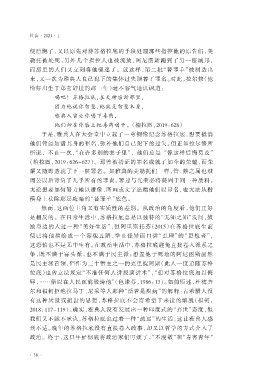Page 45 - 《社会》2021年第1期
P. 45
社会·2021·1
便后悔了,又以原先对待苏格拉底的手段处理那些指控他的原告们,美
勒托被处死,另外几个指控人也被流放,阿尼图斯跑到了另一座城邦,
而那里的人们又立刻将他驱逐了。 就这样,第二批“替罪羊”被制造出
来,又一次为雅典人自己犯下的集体过失顶替了罪名。对此,拉尔修(他
恰好出生于郑玄辞世的那一年)毫不客气地讥讽道:
喝吧! 苏格拉底,在天神宙斯那里,
因为他说你智慧,他就是智慧本身,
雅典人曾让你喝下毒药,
他们却在你唇上把毒药喝干。 (柏拉图,2019:628)
于是,雅典人在大会堂中立起了一尊铜像纪念苏格拉底,想要抵消
他们曾经加诸其身的罪名,弥补他们自己犯下的过失。 但正如拉尔修所
所说, 不止一次,“在许多别的案子里”, 他们总是“像这样后悔莫及”
(柏拉图,2019:626-627)。 那曾被指证的罪名成就了如今的荣耀,而荣
耀又随即造就了下一桩罪名。 如雅典的美勒托们一样,管、蔡之属也继
周公以后背负了几乎所有的罪责。 罪过与光荣必将凝固于同一种质料。
无论想要如何努力地以雕像、图画或文字追赠他们以显名,也无法从楷
模身上祛除那层晦暗的“替罪羊”底色。
然而,这两位主角又有实质性的差别。 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正好
是相反的。 在日常生活中,苏格拉底总是以独特的“无知之知”发问,鼓
励身边的人过一种“美好生活”,但阿里斯托芬(2015)在苏格拉底生前
便已将他描绘成一个容貌丑陋、举止怪异而口讲“歪理”的“思想者”,
这恐怕也不是无中生有。 在政治生活中,苏格拉底避免直接卷入派系之
争,既不满于寡头派,也不满于民主派;想置他于死地的阿尼图斯固然
是民主派首领,但作为三十僭主之一的克里提阿斯(此人一度追随苏格
拉底)也曾立法规定“不准任何人讲授演讲术”,“想对苏格拉底加以侮
辱,……借以在人民面前毁谤他”(色诺芬,1986:13)。如前所述,杜梅齐
尔和福柯拒绝拉马丁、尼采等人那种“活着是疾病”的解释:古希腊人没
有这种厌世或避世的思想,苏格拉底不会寄希望于来世的解脱(福柯,
2018:117-119)。确实,雅典人没有发展出一种印度式的“弃世”态度,但
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苏格拉底也过着一种“疏远”的生活,这让雅典人感
到不适。 晚年的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卷入政事,却又以哲学的方式介入了
政治。 终于,这只牛虻彻底将政治家们叮烦了,“不虔敬”和“毒害青年”
·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