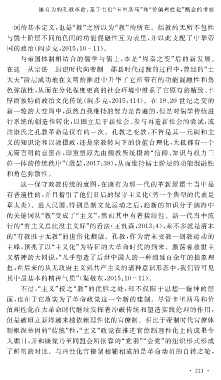Page 218 - 《社会》2019年第6期
P. 218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一词的基本定义,也是“教”之所以为“教”的所在。儒教的无所不包性
与儒士阶层不同角色间的功能混融性互为表里,并以此支配了中华帝
国的政治(阎步克, 2015 : 10-11 )。
与帝国体制相结合的儒学与儒士,本是“周秦之变”后的新发展。
在这一从宗法—封建时代向帝制—郡县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曾经的“士
大夫”阶层成功地在文明的推进中升华了它所带有的功能混融性和角
色弥散性,从而在分化程度更高的社会环境中维系了它原有的精致、丰
厚而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阎步克, 2015 : 414 )。在 19 、 20 世纪之交的
新一轮的大变局中,虽然自我维持的努力是普遍的,但是对儒学传统进
行系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图立足于新社会、参与再造新社会的尝试,或
许康氏之孔教革命是仅有的一次。孔教之变教,不管是其一元调和主
义的知识论和以教摄政,还是宗教转向下的价值合理化,大抵都有一个
无需言明的意图在,即重塑原先由儒教所统摄的“信仰、知识与权力三
位一体的传统秩序”(汲?, 2017 : 38 ),从而维持儒士阶层的功能混融性
和角色弥散性。
这一保守政教传统的意图,在康有为那一代的革新派儒士当中是
有普遍性的,并且指引了他们日后的保守主义化(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
章太炎)。进入民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趋新的知识分子脑海中
的关键词从“教”变成了“主义”,然而其中有着接续性。新一代当中流
行的“有主义总比没主义好”的看法(王?森, 2013 : 4 ),差不多就是清末
的“有教胜于无教”的世俗化翻版。孔教,作为清末变教—创教运动的
主峰,预兆了以“主义化”为特征的大革命时代的到来。激荡着救世主
义精神的大同说,“几乎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一种绵延百余年的抽象理
想,在后来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中,我们皆可见
其中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渠敬东, 2015 : 10-11 )。
不过,“主义”较之“教”的优胜之处,却不仅限于思想—精神的层
面,也在于它落实为了革命政党这一全新的建制。尽管卡里斯马和价
值理性化在大革命时代继续发挥着冲破传统和塑造实践伦理的作用,
但是破旧立新将越来越依赖理性化的官僚制。相比于帝制时代官僚体
制根深蒂固的“传统”性,“主义”政党在推进官僚制理性化上的成果令
人瞩目,并和康党乃至同盟会所依靠的“党羽”“会党”的组织形式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与理性化官僚制相辅相成的是革命动员的自转之轮,
· 2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