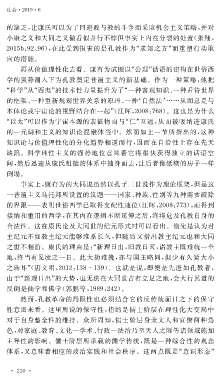Page 217 - 《社会》2019年第6期
P. 217
社会· 2019 · 6
的缺乏,让康氏可以为了回避政与教的斗争而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并对
小康之义和大同之义做看似并行不悖但事实上内在分裂的处置(张翔,
2015犫 : 92 、 96 ),在此受到损害的是孔教作为“求知之方”而重塑行动取
向的潜能。
再从价值理性化去看。康有为试图以“公理”话语的建构在世俗西
学的强势涌入下为孔教奠定普遍主义的新基础。作为一种策略,他把
“科学”从“西夷”的技术性力量提升为了“一种客观知识、一种看待世界
的框架、一种重新规划世界关系的原理、一种‘自然法’……从而总是与
本体论或宇宙论的视野结合在一起”(汪晖, 2008 : 768 )。这也是为什么
“以太”可以作为宇宙本源的表征物而与“仁”互通,从而被吸纳进康氏
的一元调和主义的知识论混融体当中。然而如上一节所指出的,这种
知识论与价值理性化的分化趋势相逆而行,因而在自洽性上存在先天
缺陷。科学理性主义的强势地位意味着它将很快获得独立的话语空
间,然后迅速从康氏粗拙的体系中抽身而去,让后者像纸糊的房子一样
倒塌。
事实上,康有为的大同说虽然以孔子三世说作为理论框架,但是这
一普遍主义乌托邦所设置的议题———国家、种族、性别等九种需要破除
的界限———表明世俗西学已取得支配性地位(汪晖, 2008 : 773 ),而得到
接纳和重用的西学,在其内在逻辑不断延伸之后,终将危及孔教自身的
合法性。这在康氏论及大同世的纪元形式时可以看出。他先是认为君
主纪元不如教主纪元能够维系长久,但随后又指出教主纪元也和大同
之世不相洽。康氏的理由是:“新理日出,旧教日灭,诸教主既难统一全
地,终当有见废之一日。此大劫难挽,亦与国主略同,但少有久暂大小
之殊耳”(唐文明, 2012 : 138-139 )。也就是说,即便是先进如孔教者,
由于“新理日出”的大势,也无法在大同世占有立足之地,会大行其道的
反倒是仙学和佛学(郭鹏等, 1989 : 242 )。
然而,孔教革命的局限性也必须结合它的反传统面目之下的保守
性意图来看。这里所说的保守性,指的是儒士阶层在理性化大变局中
对于自身整全性的维持。众所周知,儒士阶层身兼文人和官僚两种角
色,对家庭、教育、文化—学术、行政—法治乃至天人之际等诸领域施加
主导性的影响。儒士阶层所承载的儒学传统,既是一种综合性的观念
体系,又意味着相应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秩序。这两点既是“意识形态”
· 2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