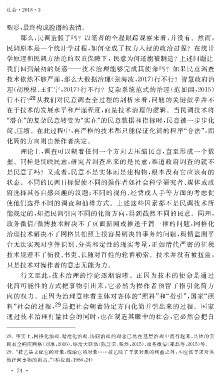Page 81 - 《社会》2018年第3期
P. 81
社会· 2018 · 3
塑形,最终构成脸谱的表情。
那么,民调造假了吗?以笔者的全程跟踪观察来看,并没有。然而,
民调原本是一个统计学过程,如何变成了权力入侵的政治过程?在统计
学原理和民调方法论的双重保障下,民意为何还能被制造?上述问题让
我们回到最初的疑惑———技术治理能够完成其使命吗?如果民意调查
技术依然不够严谨,那么大数据治理(张海波, 2017 )行不行?智慧政府治
理(胡税根、王汇宇, 2017 )行不行?复杂系统范式的治理(范如国, 2015 )
行不行? 28 从我们对民意调查全过程的剖析来看,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
在于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严谨程度,而是技术治理的逻辑。当民调技术将
“潜在”的复杂民意转变为“实在”的民意数据和指标时,民意被一步步化
简、压缩。在此过程中,再严格的技术都只能保证化简的程序“合法”,而
化简的方向则由操作者决定。
理论上,调查可以朝着任何一个方向去压缩民意,直至形成一个数
据。同样是反映民意,研究者调查出来的是民意,难道政府调查的就不
是民意了吗?又或者,民意不是实体而是建构物,根本没有它应该有的
状态。不同的民调目标促使不同的操作者如社会科学研究者、媒体或政
府选择其各自感兴趣的议题;不同的视角、经费或人手等方面的考虑促
使他们选择不同的调查和抽样方式。上述这些因素都不是民调技术所
能规定的,却把民调引向不同的化简方向,得到截然不同的民意。同理,
政务微信/微博技术解决不了页面新闻或推送千篇一律的问题,网格化
治理技术解决不了网格员拍照上报容易解决的事务的问题,舆情监测平
台无法实现对事件识别、分类和定性的现实考量,正如清代严密的征税
技术规避不了衙役、书吏、长随对百姓的轮番勒索。技术并没有被扭曲,
只是技术对操作者的意志无能为力。
行文至此,技术治理的悖论逐渐清晰。正因为技术的使命是通过
化简可能性的方式把事物引出来,它必然为操作者预留了指引化简方
向的权力。正因为治理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照料”和“指引”,国家“照
料”社会的过程, 29 是把社会朝着特定方向化简并引出来的过程。国家
通过技术治理打量社会的同时,也在制造其眼中的社会,它必然会把自
28. 事实上,网格化治理、精准化治理、协同治理的理念已然在基层治理中流行起来,具体的实
践有全响应网格(刘冰, 2016 )、综治大联动(陈慧荣、张煜, 2015 )、政务微信(郑磊等, 2015 )等。
29. “技艺是支配它的对象,统治它的对象……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之外,不应该寻求对其
他任何事物的利益。”(柏拉图, 1986 : 24 )
· 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