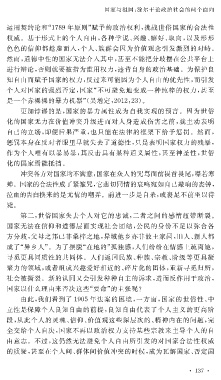Page 144 - 《社会》2017年第6期
P. 144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运用契约论和“ 1789 年原则”赋予的政治权利,挑战世俗国家的合法性
权威。基于形式上的个人自由,各种学说、兴趣、癖好、取向,以及形形
色色的信仰都趁虚而入,个人、族群会因为价值观念引发激烈的对峙。
然而,道德中性的国家无法介入其中,甚至不能把分歧摆在公共平台上
进行辩论,否则就要被指为滥用权力,违背自身的政治基础。为保护良
知自由而赋予国家的权力,反过来可能因为个人自由的优先性,而引发
个人对国家的强烈否定,国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纯粹的权力,甚至
是一个赤裸裸的暴力机器”(吴增定, 2012 : 23 )。
更加悖谬的是,国家的暴力属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世俗
化的国家无力在价值冲突升级进而对人身造成伤害之前,就主动表明
自己的立场,即便后果严重,也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给予惩罚。然而,
惩罚本身在反对者眼里早就失去了道德性,只是表明国家权力的残暴,
作为个人唯有以暴易暴,其反击具有某种道义属性,甚至神圣性,世俗
化的国家焉能抵挡。
冲突各方对国家均不满意,国家在众人的咒骂面前畏首畏尾,噤若寒
蝉。国家的合法性成了紧箍咒,它悲切同情的哀鸣宛如自己敲响的丧钟,
泣血的告白换来的是无情的嘲弄。前进一步是自杀,或裹足不前坐以待
毙。
第二,世俗国家失去个人对它的忠诚,二者之间的感情纽带断裂。
国家无法在信仰和道德层面实现社会团结,公民的身份不足以弥合各
方分歧,父母之邦已非桑梓之地,异域他乡亦非故土家园,旧人、新人都
成了“异乡人”。为了摆脱“在地的”孤独感,人们纷纷在情感上疏离她,
寻觅更具同质性的共同体。人们返回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等更具凝
聚力的领域,或者组成兴趣爱好相近的、碎片化的团体,重新寻觅归所,
社会被撕裂。新的认同又会引发种种自主的诉求,进而反作用于政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否决这些“要命”的主张呢?
由此,我们看到了 1905 年法案的困境,一方面,国家的世俗性、中
立性是保障个人良知自由的前提,良知自由代表了个人主义的更高阶
段,从此个人的灵魂、信仰、价值观这些深层次的、精神内在的问题,完
全交给个人自决,国家不再以政治权力支持某些宗教来主导个人的自
由意志。不过,这仍然无法避免个人自由所引发的对国家合法性权威
的质疑,甚至在个人间、群体间价值冲突的时候,成为瓦解国家、否定国
· 1 3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