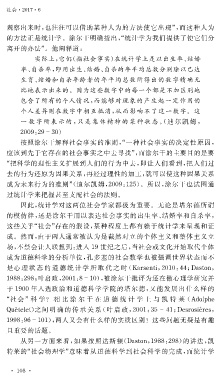Page 115 - 《社会》2017年第6期
P. 115
社会· 2017 · 6
观察出来时,也往往可以借助某种人为的方法使它出现”,而这种人为
的方法正是统计学。涂尔干明确指出,“统计学为我们提供了使它们分
离开的办法”。他阐释道:
实际上,它们(指社会事实)在统计学上是以出生率、结婚
率、自杀率,即用出生、结婚、自杀的年平均总数分别除以已达
生育、结婚和自杀年龄者的年平均总数所得出的数字精确无
比地表示出来的。因为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都是不加区别地
包含了所有的个人情况,而能够对现象的产生起一定作用的
个人差异则在数字中相互抵消,从而影响不了这一数字。这
一 数 字 所 表 示 的 ,只 是 集 体 精 神 的 某 种 状 态 。(迪 尔 凯 姆 ,
2009 : 29-30 )
按照涂尔干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
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涂尔干的主要目的是要
“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
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
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迪尔凯姆, 2009 : 125 )。所以,涂尔干也试图通
过统计学来把握甚至支配社会的法则。
因此,统计学对这两位社会学家都极为重要。无论是塔尔德所谓
的模仿律,还是涂尔干用以表达社会事实的出生率、结婚率和自杀率,
这些关乎“社会”存在的假设,某种程度上都有赖于统计学来呈现和证
成。然而,由于两人通常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立
场,不禁会让人联想到:进入 19 世纪之后,当社会或文化开始取代个体
成为道德科学的分析单位,孔多塞的社会数学也被强调世界状态而不
是心 理 状 态 的 道 德 统 计 学 所 取 代 之 时 ( 犓犪狉狊犲狀狋犻 , 2010 : 44 ; 犇犪狊狋狅狀 ,
1988 : 298 ;叶启政, 2001 : 8-10 ),被涂尔干批评为还在做心理学研究并
于 1900 年入选政治和道德科学学院的塔尔德,又能发展出什么样的
“社 会 ”科 学? 相 比 涂 尔 干 在 道 德 统 计 学 上 与 凯 特 莱 ( 犃犱狅犾 狆 犺犲
犙狌é狋犲犾犲狋 )之间 明 确 的 传 承 关 系 (叶 启 政, 2001 : 35-41 ; 犇犲狊狉狅狊犻è狉犲狊 ,
1998 : 96-101 ),两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实质区别?这些问题无疑是有趣
且重要的话题。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按照达斯顿( 犇犪狊狋狅狀 , 1988 : 298 )的讲法,凯
特莱的“社会物理学”意味着从道德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完成,而统计学
· 1 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