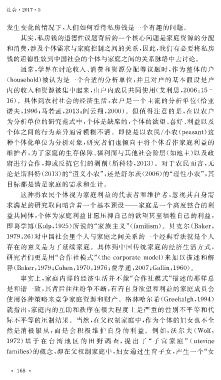Page 175 - 《社会》2017年第5期
P. 175
社会· 2017 · 5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看待私房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其实,私房钱的道德性议题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家庭资源的分配
和消费,涉及个体需求与家庭控制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私房
钱的道德性放到中国社会的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脉络中去讨论。
通常,学界在讨论收入、消费和资源分配等议题时,作为整体的户
( 犺狅狌狊犲犺狅犾犱 )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并且对户的基本假设是户
内的收入和资源被集中起来,由户内成员共同使用(艾利思, 2006 : 15-
16 )。具体到农村社会的经济生活,农户是一个主流的分析单位(恰亚
诺夫, 1996 ;马若孟, 2013 ;阎云翔, 2000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农户
为分析单位的研究范式中,个体是缺席的,个体的欲望、喜好、利益以及
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通常模糊不清。即使是以农民/小农( 犲犪狊犪狀狋 )这
狆
种个体化单位为分析对象,研究者们也倾向于将个体看作家庭利益的
维护者,为了家庭的生存保障、福利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地主)以及政
府进行合作,抑或反抗它们的剥削(斯科特, 2013 )。对于农民而言,无
论是斯科特( 2013 )的“道义小农”,还是舒尔茨( 2006 )的“理性小农”,其
目标都是满足家庭的需求和生计。
这种将农民个体视为家庭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忽视其自身需
求满足的研究取向暗含着一个基本预设———家庭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利
益共同体,个体为家庭利益甘愿压抑自己的欲望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
,
即葛学博( 犓狌犾 狆1925 )所说的“家族主义”( 犳犪犿犻犾犻狊犿 )。贝克尔( 犅犪犽犲狉 ,
1979 : 26 )对中国社会里个人与家庭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看法就是个人
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延续家庭。具体到中国传统家庭的经济生活方式,
研究者们更是用“合作社模式”( 狋犺犲犮狅狉 狆 狅狉犪狋犲犿狅犱犲犾 )来加以描述和解
释( 犅犪犽犲狉 , 1979 ; 犆狅犺犲狀 , 1970 , 1976 ;费孝通, 2007 ; 犌犪犾犾犻狀 , 1960 )。
事实上,家庭内部的经济生活并不像“合作社模式”描述的那样总
是和谐一致,其背后往往纷争不断,有着自身欲望和利益的家庭成员会
使用各种策略来竞争家庭资源和财产。格林哈尔希( 犌狉犲犲犺犪犾 犵 犺 , 1994 )
就指出,家庭内的互助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代
际不平等的压制结果。当然,在父权制家庭中,作为个体的妇女也不全
然是消 极 服 从,而 是 会 积 极 维 护 自 身 的 利 益。例 如,沃 尔 夫 ( 犠狅犾犳 ,
1972 )基 于 在 台 湾 地 区 的 田 野 调 查,提 出 了 “子 宫 家 庭 ”( 狌狋犲狉犻狀犲
犳犪犿犻犾犻犲狊 )的概念,即在父权制家庭中,妇女通过生育子女,产生一个“女
· 1 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