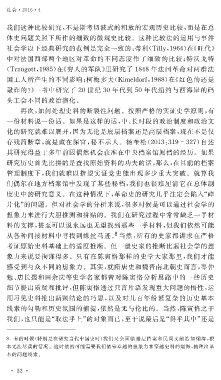Page 39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39
社会· 2016 · 4
我们这种比较研究,不是斯考切波式的粗放的宏观历史比较,而是在总
体史问题关照下所作的细致的微观史比较。这种比较法的运用与事件
社会学以下经典研究的范例是完全一致的:蒂利( 犜犻犾犾 狔1964 )在《旺代》
,
中对法国西部两个地区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作了细致的比较;特沃戈特
( 犜狉犪狌 犵 狅狋狋 , 1985 )在《穷人的军队》里研究了 1848 年法国革命对两群法
国工人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柯梅多夫( 犓犻犿犲犾犱狅狉犳 , 1988 )在《红色的还是
敲诈的?》一书中研究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纽约与西海岸的码
头工会不同的政治演化。
再次,如何处理史料的断裂性问题。按照严格的实证史学原则,有
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中、长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
化的研究就难以展开,因为无论是底层档案还是高层档案,现在不是仅
存残简断章,就是藏在深宫,秘不示人。杨奎松( 2013 : 319-327 )自述
其研究得益于多年前因偶然机会获准在中央档案馆阅档的经历。如果
研究历史首先比拼的是查找原始资料的功夫的话,那么,在目前的档案
管理制度下,我们就难以指望实证党史能出现多少重大突破。就算我
们偶尔在地方档案馆中发现了某些秘档,我们也很难厘清它在总体制
度史中的研究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史的研究几乎注定会陷入“碎
片化”的问题。但对社会学的分析来说,很多时候是可以通过社会学的
想象力来进行大胆推测和拼贴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常缺乏一手材
料的支撑,甚至可以说永远也无望找到那些一手材料,但我们依然可能
从各种间接材料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8 当然,所有的史家都讲求在严格
考证原始史料基础上的适度推断。但一般史家的推断比起社会学的想
象力来说要拘谨得多。只有在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家那里,我们才能
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想象力。其实,就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岑仲
勉、唐长孺和田余庆等史学名家都曾对陈寅恪分析思路中的一些历史
细节提出质疑和批评,但陈寅恪透过只言片语发现重大问题的悟性,运
用习见史料推出新颖结论的巧思,以及对几百年纷繁复杂的历史基本
线索的勾勒和历史氛围的捕捉,依然是无与伦比的。当然,陈寅恪之于
我们,也只能是“取法乎上”的对象而已,至于说最后是“得乎其中”还是
8. 有的时候(特别是在研究当代中国史时)我们又会面临基层档案和民间文献浩如烟海,根
本无法尽读的情况。这时依然可能需要我们依靠卓越的想象力来穿越史料的烟海,梳理出基
本的问题线索。
·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