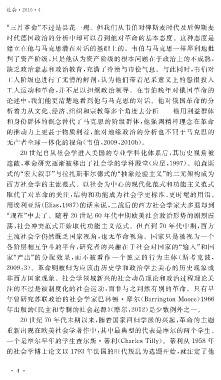Page 11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11
社会· 2016 · 4
“三月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我们从韦伯对俾斯麦时代及后俾斯麦
时代德国政治的分析中却可以看到他对革命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是
建立在他与马克思潜在对话的基础上的。韦伯与马克思一样犀利地批
判了资产阶级,只是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上的不成熟,
缺乏政治意志和政治教育,充满了冷漠与市侩气息。与此同时,韦伯对
工人阶级也进行了无情的解剖,认为他们带着尼采意义上的怨恨投入
工人运动和革命,并不足以担纲政治领导。在韦伯晚年对俄国革命的
论述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他与马克思的对话。他对俄国革命的分
析着力从文化、经济、组织和宗教等多个角度去分析———他用利益群体
和身份群体的概念替代了马克思的阶级群体,他强调精神理念在革命
的推动力上更甚于物质利益,他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也不同于马克思的
无产者全球一体化的视角(韦伯, 2009 , 2010犫 )。
20 世纪自从社会学进入美国的专业学科化体系后,其历史视角被
遮蔽,革命研究逐渐被移出了社会学的学科殿堂(应星, 1997 )。帕森斯
式的“宏大叙事”与拉扎斯菲尔德式的“抽象经验主义”的二元架构成为
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范式。以社会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和功能主义范式
取代了对革命的关注,结构和功能成为社会学更标准、更时髦的用语。
用埃利亚斯( 犈犾犻犪狊 , 1987 )的话来说,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学家大多退却到
“现在”中去了。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欧美社会政治形势的剧烈震
荡,社会冲突范式开始取代功能主义范式。但直到 70 年代中期,西方
主流社会学仍然既乏国家视角,也无革命视角。国家只是被视为一个
各阶层相互争斗的平台,研究者的兴趣在于社会对国家的“输入”和国
家“产出”的分 配 效 果,而 不 被 看作 一个独 立的 行为主 体(斯考 克波,
2009 : 3 )。革命则被归为应该由历史学和政治学去关心的历史现象或
非西方国家现象。社会学领域新兴的社会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关
注的不过是被制度化的社会运动,而非与之判然有别的革命。只有早
年曾研究苏联政治的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 犅犪狉狉犻狀 犵 狋狅狀犕狅狅狉犲 ) 1966
年出版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摩尔, 2012 )是少数例外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家回归学派的兴起,革命的主题
重新出现在欧美社会学著作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摩尔的两个学生。
一个是摩尔早年的学生查尔斯·蒂利( 犆犺犪狉犾犲狊犜犻犾犾 狔 )。蒂利从 1958 年
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以 1793 年法国的旺代叛乱为选题开始,就注定了他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