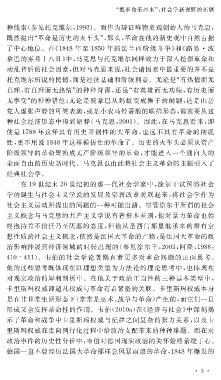Page 10 - 《社会》2016年第4期
P. 10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种线索(参见托克维尔, 1992 )。而作为辩证唯物史观创始人的马克思,
既然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革命在他的新史观中自然占据
了中心地位。在《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与托克维尔同样致力于深入挖掘革命和
动乱背后的社会因素,但对马克思来说,社会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
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而是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无论是“有热情而无
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的种种背谬,还是“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
无事变”的种种错位;无论是波拿巴从蚂蚁变成狮子的闹剧,还是山岳
党人虚张声势的可笑表演,或是小农马铃薯般的联结形态,都需要从这
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得到解释(马克思, 2001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即
使是 1789 年这样具有历史开创性的大革命,也远不具有革命的彻底
性,更不用说 1848 年这样模仿性的革命了。历史的火车头必须从资产
阶级领导的革命置换成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进入一个通向人的
全面自由的历史新时代。马克思也由此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引入了
经典社会学。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那一代社会学家中,涂尔干试图将社会
学的诞生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及宗教改革关联起来,将社会学作为
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可能出路。尽管涂尔干所谓的社会
主义概念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着根本差别,他对暴力革命也始
终抱持着不信任乃至厌恶的态度,但他从圣西门那里继承来的带有空
想性质的社会主义概念,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法国大革命的政
治影响伸展到经济领域的时候出现的(参见涂尔干, 2003 ;阿隆, 1988 :
410-411 )。韦伯的社会学论著则有着更多对革命问题的正面思考。
他的这些思考既体现在以理想类型为方法论的理论思考中,也体现在
对现实政治的犀利剖析中。在他关于政治正当性的三种基本类型中,
卡里斯玛权威即超凡权威与革命有着紧密的关联。卡里斯玛权威本身
是在非日常生活形态下(常常是巫术、战争与革命)产生的,而它们一旦
形成又会发挥革命性的作用。韦伯( 2010犪 )在《经济与社会》中深刻揭
示了革命和战争中卡里斯玛权威与纪律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以及卡
里斯玛权威在走向例行化过程中给政治支配带来的种种难题。而在对
政治事件的历史性分析中,韦伯对德国现实政治的关怀始终萦绕于心。
德国一直不曾经历法国大革命那样急风暴雨般的革命, 1848 年爆发的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