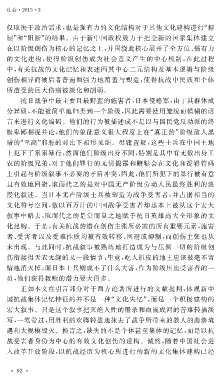Page 99 - 《社会》2015年第3期
P. 99
社会· 2015 · 3
仅取决于政治需求,也是强有力的文化结构对于其他文化建构进行“抑
制”和“阻断”的结果。由于新中国政权致力于把全新的国家集体建立
在以阶级创伤为核心的记忆之上,并围绕此核心展开了全方位、强有力
的文化建构,使得阶级创伤成为社会意义产生的中心机制,在此过程
中,有关抗战的文化记忆和表述因其中心二元结构及基本逻辑与阶级
创伤相异而被后者普遍和强力地覆盖与塑造,使得抗战中民族和个体
所遭受的巨大伤痛被淡化和削弱。
抗日战争中最主要且最野蛮的施害者,日本侵略军,由于其群体成
分异质,不能被简单地归类到一个阶级,因此需要使用笼统而模糊的语
言来进行文化编码。他们的行为被描述成不足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终
极卑鄙相提并论,他们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在“真正的”阶级敌人黑
暗的“至高”邪恶的对比下相形见绌。毋庸置疑,这些士兵在中国土地
上犯下了累累暴行,然而他们阶级出身不同,特别是其中有无数出身工
农的阶级兄弟,对于他们罪行的无情揭露和鞭鞑会在文化和逻辑符码
上引起与阶级叙事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因此,他们所犯下的暴行被有意
且有效地回避,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最终胜利的浪
漫化叙述。当日本无产阶级士兵被塑造为战争受害者,并占据相当的
文化符号空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却基本上被从这个宏大
叙事中略去,取而代之的是堂而皇之地赋予抗日英雄高大全形象的文
化建构。于是,有关抗战的潜在创伤主张所必需的所有重要元素,施害
者、受害者以及受难性质均被有效转移、回避或抑制,而创伤主张也从
未出现。与此同时,抗战叙事被熟练地打造成为与压倒一切的阶级创
伤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又一段情节:毕竟,吃人扒皮的地主应该被毫不留
情地消灭掉,而日本士兵则成不了什么大害,作为阶级压迫受害者的一
员,他们获得救赎的潜力要大得多。
正如本文在引言部分对于西方论著所进行的文献批判,体现新中
国抗战集体记忆特征的并不是一种“文化失忆”,而是一个积极建构的
宏大叙事。只是这个叙事把灭绝人性的屠杀和血流成河的苦难轻描淡
写,一笔带过,用胜利的欢腾轻盈地抹去了战争所带来的骇人的悲惨境
遇和大规模毁灭。换言之,缺失的不是个体甚至集体的记忆,而是以抗
战受害者身份为中心的有效文化创伤的建构。诚然,随着中国社会进
入改革开放阶段,以抗战经历为核心所进行的新的文化集体建构已经
· 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