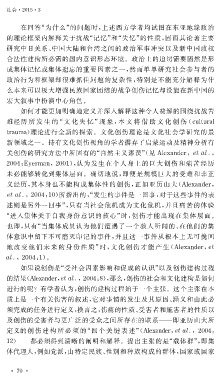Page 77 - 《社会》2015年第3期
P. 77
社会· 2015 · 3
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时,上述西方学者均试图在东亚地缘政治
的理论框架内解释关于抗战“记忆”和“失忆”的性质,因而其论著主要
研究中日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以及新中国政权
合法性建构所必需的国内意识形态环境。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固然是形
成集体记忆或集体遗忘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单单研究社会参与者的
政治行为和框架却很难抓住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不能充分解释为什
么本来可以极大增强民族国家团结的战争创伤记忆却没能在新中国的
宏大叙事中扮演中心角色。
如何才能更加明确地定义并深入解释这种令人费解的围绕抗战苦
难经历 所 发 生 的 “文 化 失 忆”现 象,本 文 将 借 助 文 化 创 伤 (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狋狉犪狌犿犪 )理论进行全新的探索。文化创伤理论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最
新领域之一。持有文化创伤视角的学者摒弃了启蒙运动及精神分析有
关创伤的研究方法中所固有的“自然主义谬误”(见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 犲狋犪犾. ,
2004 ; 犈 狔 犲狉犿犪狀 , 2001 ),认为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巨大创伤和痛苦经历
未必能够转化到集体层面。确切地说,即便是规模巨大的受难和非正
义经历,其本身也不能构成集体性的创伤,正如亚历山大(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
犲狋犪犾. , 2004 : 10 )所指出的,“发生的事件是一回事,对于这些事件的表
述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当社会危机成为文化危机,并且痛苦的体验
“进入集体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才能出现在集体层面。
也即,只有“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在他们的集
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
地改 变 他 们 未 来 的 身 份 性 质”时,文 化 创 伤 才 能 产 生 (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 犲狋
犪犾. , 2004 : 1 )。
如果说创伤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促成的认识”以及创伤建构过程
的结果(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 犲狋犪犾. , 2004 : 8 ),那么,创伤的社会和文化建构是如何
进行的呢?有学者认为,创伤的建构过程始于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在本
质上是一个有关伤害的叙述,它对事情的发生及其原因、涵义和由此必
须完成的任务进行定义,换言之,伤痛的性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性质以
及创伤的受害者与更广泛的受众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即亚历山大所
定义的创 伤 建 构 所 必 须 的 “四 个 关 键 表 述”( 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 , 犲狋犪犾. , 2004 :
12 )———都必须得到清晰的阐明和解释。提出主张的是“载体群”,即集
体代理人,例如党派,由特定民族、性别和种族构成的群体,国家或国家
· 7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