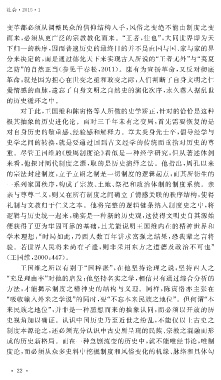Page 29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29
社会· 2015 · 1
变革都必须从调整民众的信仰结构入手,风俗之变绝不能由制度之变
而来,必须从更广泛的宗教教化而来。“王者,往也”,大同世界即为天
下归一的秩序,因而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国与国、家与家的界
分来决定的,而是通过德化天下来实现古人所说的“王者无外”与“夷夏
之防”的自然正当(参见干春松, 2011 )。康有为宣扬革命,又反对彻底
革命,就是因为担心在世变之亟和政变之际,人们割断了自身文明之仁
爱情感的血脉,遗忘了自身文明之自然史的演化次序,永久落入据乱世
的历史循环之中。
对于此,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所做的史学矫正,针对的恰恰是这种
极其抽象的历史进化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首先需要恢复的是
对自身历史的敬重感、经验感和解释力。章太炎身先士卒,倡导经学与
史学之间的转换,就是要通过回到古文经学的传统而重拾对历史的尊
重。尽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看似是一种经学研究,但从著述体例
来看,他探讨周代制度之源,取的是历史演绎之法。他指出,周孔以来
的宗法封建制度,立子立嗣之制是一切制度的逻辑起点,而其所衍生的
一系列家国秩序,构成了宗族、土地、祭祀和政治体制的制度系统。亲
亲与尊尊二义,则又在所有制度之间确立了情感关联的秩序结构,使得
礼制与文教归于仁义之本。他将完整的逻辑链条纳入制度史之中,将
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确实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使得文明史自其源始
便获得了更为牢固可靠的基础,且尤能说明王国维内在的精神世界和
学术理想:“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
验。若世界人民将来尚有孑遗,则非采用东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 王国维, 2000 : 447 )。
王国维之所以有别于“国粹派”,在他坚持论理之说,坚持西人之
“充足理由率”对他的启发;他坚持名实之学,相信只有通过综合分析的
方法,才能揭示制度之精神史的结构与义理。同样,陈寅恪亦主张在
“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何谓“本
来民族之地位”,并非是一种臆想而来的抽象认同,而必须以开放的历
史视角加以确证。认识中国历史乃至近世之纷乱,不能仅以上古史之
制度本源论之,还必须充分认识中古史所呈现的民族、宗教之混融而形
成的历史新格局。而在一种急剧流变的历史中,就不能唯经书论,唯制
度论,而必须从众多史料中挖掘制度和风俗变化的机缘、脉络和具体勾
·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