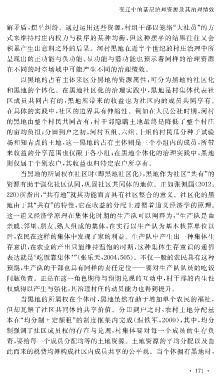Page 178 - 《社会》2014年第1期
P. 178
变迁中的基层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绩效
解矛盾,摆平纠纷。通过运用这些资源,村组干部以笼络“大社员”的方
式来维持村庄内权力与秩序的某种均衡,但这种摆平的结果往往又会
积累产生出意料之外的后果。河村黑地在近半个世纪的村庄治理中所
呈现出的正功能与负功能、显功能与潜功能也预示着同样的治理资源
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中可能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
以黑地的占有主体来区分黑地的资源属性,可分为黑地的社区化
和黑地的个体化。在黑地社区化的治理实践中,黑地是村集体代表社
区成员共同占有的,黑地所带来的收益也为社区内的成员共同享有。
在具体的实践中,社区的边界具有伸缩性。例如在人民公社时期,河村
的黑地由整个村民共同占有,村干部隐瞒土地最终是降低了整个村庄
的亩均负担;分田到户之初,河村五组、六组、十组的村民瓜分种子试验
场和知青点的土地,这一黑地的占有主体则是三个小组内的成员,所带
来收益的分享范围也仅限于各小组;在黑地个体化的治理实践中,黑地
则仅属于个别农户,其收益也归特定农户所享有。
当黑地的所属权在社区时(即黑地社区化),黑地作为社区“共有”的
资源有助于强化社区认同,巩固社区共同体的地位。正如张佩国( 2012 :
220 )所指出,“共有地”就其功能而言具有社区整合的意义。社区化的黑
地由于其“共有”的特性,它在收益的分配上遵循着道义经济学的原理。
这一道义经济学原理在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可以阐释为,“生产队是由
亲戚、邻里、朋友、熟人组成的集体,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
后,农民在这样的集体中发现了家的利益。生产队中产生出一种集体生
存意识,在农业的产出只能维持温饱的时期,这种集体生存意识的通俗
表达就是‘吃饭靠集体’”(张乐天, 2004 : 505 )。不仅一般的农民具有这种
预期,生产队的干部也具有同样的责任定位———要对生产队队员的吃饭
问题负责。正是在这一角色期待与预期兑现的互动中,村干部的内生性
权威得以产生与强化,其治理村庄的动员能力也得到提升。
当黑地的所属权在个体时,黑地虽然有助于增加单个农民的福祉,
但却瓦解了社区共同体的共享价值。分田到户之时,农村土地分配基
本在“均分制 + 定额租”的制度框架内完成(温铁军, 2000 ),其中,均分
制强调了社区成员权的存在与兑现,村集体要对每一个成员的生存负
责,要给每一个成员分配均等的土地资源。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以及由
此而来的税费均摊构成社区内成员共享的公平观。当个体拥有黑地时,
· 1 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