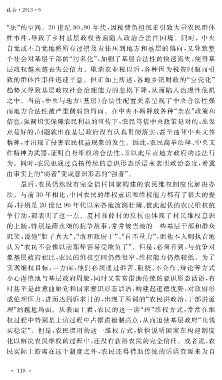Page 125 - 《社会》2013年第6期
P. 125
社会· 2013 · 6
“法”的空间。 20 世纪 80 、 90 年代,因税费负担沉重引致大量农民群体
性事件,导致了乡村基层政权普遍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同时,中央
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所有过错及责任压到地方和基层的偏向,又导致整
个社会对基层干部的“污名化”,加剧了基层合法性的快速流失,使得基
层政权越来越丧失公信力。取消农业税以后,各种因为税费问题而引
致的群体性事件迅速平息。但正如上所述,各地乡镇财政的“空壳化”
趋势又导致基层政权社会治理能力的急剧下降,从而陷入治理性危机
之中。当前,中央与地方(基层)合法性配置关系呈现了中央合法性强
而地方合法性被严重削弱的局面。在中央不断释放各种“亲农”政策和
信息,强调切实保障农民利益的宣传下,农民笃信中央政策是对的,出发
点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基层政府没有认真贯彻落实,甚至违背中央文件
精神,才出现了侵害农民权益现象的发生。因此,农民高举法律、中央文
件精神为武器,证明自身维权的合法性,并以此斥责地方政府的违法行
为。同时,农民也通过高扬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表明政治态度,希冀
由事实上的“弱者”变成意识形态的“强者”。
最后,农民仍然没有完全信任国家构建的农民维权制度化解决办
法。与前 30 年相比,中国农民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
高,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各地波澜壮阔、彼此起伏的农民维权抗
争行动,都表明了这一点。厦村和薛村的反抗也体现了村民维权意识
的上扬,特别是薛永颂的抗争故事,常常被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
讥笑,说他“胆子真大”、“敢和政府干”、“自不量力”,而他本人则执着地
认为“农民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受欺负了”。但是,必须看到,与抗争对
象基层政府相比,农民的维权空间仍然很窄,维权能力仍然较低。为了
实现维权目标,一方面,他们必须通过诉苦、阻挠、不合作、辩论等方式
小心谨慎地与基层政府周旋,同时又常常借助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有
时甚至是故意曲解党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构建起道德优势,对政府形
成伦理压力,进而达到诉求目的,出现了所谓的“农民讲政治,干部讲道
理”的尴尬局面。从表面上看,农民的这一讲“理”维权方式,常常在维
权过程中特别是上访过程中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迫使基层政府“花钱
买稳定”。但是,农民惯用的这一维权方式,恰恰说明国家在构建制度
化以解决农民维权的过程中,还没有获得农民的完全信任。或者说,农
民实际上游离在这个制度之外,农民还得借助传统的话语资源来为自
· 1 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