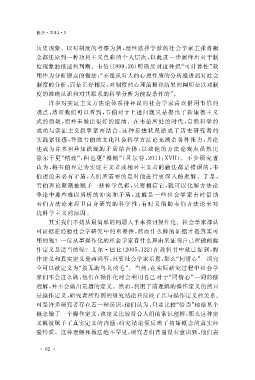Page 69 - 《社会》2013年第5期
P. 69
社会· 2013 · 5
历史现象。以对制度的考察为例,理性选择学派的社会学家主张将概
念都还原到一种功利主义色彩的个人层次,以此进一步演绎出对于制
度现象的描述和判断。韦伯( 1999 : 26 )明确反对这种把“可计算性”效
用作为分析原点的做法:“不是从对人的心理性质的分析推进到对社会
制度的分析,而是正好相反,对制度的心理前提和结果的阐明是以对制
度的准确认识和对其联系的科学分析为前提条件的”。
许多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体系持异议的社会学家喜欢借用韦伯的
观点,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韦伯对于上述问题只是提出了新康德主义
式的质疑,而并未做出很好的澄清。在韦伯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的
成功与实证主义叙事紧 密结合,这种 思想状况 造成了历 史研 究者 的
实践紧张感,导致韦伯的文化社会科学方法论充满着各种张力,其论
述成为许多相异知识观 的矛盾 结合 体,以致 他 的方法论 观点 虽然 比
涂尔干更“精致”,但也更“模糊”(贝尔 特, 2011 : 犡犞犐犐 )。不 少研 究者
认为,将韦伯界定为实证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韦
伯理论未必有矛盾,人们所需要的是对他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于是,
韦伯理论渐渐被赋予一些神学色彩,只要相信它,就可以化解方法论
争论中那些难以辨析的 冲突和 矛盾,这就是一 些社会学 家有 时借 助
韦伯方法论来捍卫自身 研究的 科学 性,有时 又 借助韦伯 方法 论来 对
抗科学主义的原因。
其实我们不妨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来探讨操作化。社会学家都认
可证据在经验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然而什么样的证据才是真实可
用的呢?一位从事操作化的社会学家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自己所做的操
作定义是适当的呢?艾尔·巴比( 2005 : 122 )在教科书中就已提到,操
作定义和真实定义是两码事,只要社会学家乐意,那么“同情心”一词完
全可以被定义为“拔无助鸟儿的毛”。当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社会学
家们不会这么做,他们在操作化时会利用自己对于“同情心”一词的前
理解,并不会做出荒唐的定义。然而,利用了前理解的操作定义仍然只
是操作定义,研究者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只反映了其与操作定义的关系。
可是许多研究者存在着一种误识,他们认为,只要比较“恰当”地给某个
概念做了一个操作定义,该定义比较符合人们的常识理解,那么这种定
义就被赋予了真实定义的内涵,研究结论便反映了初始概念的真实经
验特质。这种理解和做法绝不罕见,研究者们普遍没有意识到,他们表
· 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