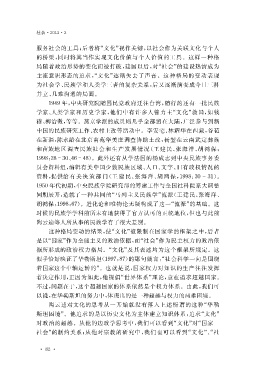Page 89 - 《社会》2013年第2期
P. 89
社会· 2013 · 2
服务社会的工具;后者将“文化”视作关键,以社会作为关联文化与个人
的桥梁,同时将其当作实现文化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工具。这样一种格
局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被打破,建国以后,对“社会”的建设热情成为
主流意识形态的追求,“文化”逐渐失去了声音。这种格局的变动表现
为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三者的复杂关系,后又逐渐演变成今日三科
并立、几难沟通的局面。
1949 年,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随行的还有一批民族
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力主“文化”救国,如钱
穆、柳诒徵,等等。燕京学派的成员则几乎全部留在大陆,广泛参与到新
中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农村土改等活动中。李安宅、林耀华在西藏,谷苞
在新疆,陈永龄在北京南苑华美庄调查协助土改,杨在云南武定彝族
和苗族地区调查民族社会和生产发展情况(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
1998 : 28-30 、 46-48 )。此外还有从学法国的杨成志到中央民族事务委
员会资料组,编辑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区域、人口、文字、旧有政权情况的
资料,提供给 有 关 决 策 部 门(王 建 民、张 海 洋、胡 鸿 保, 1998 : 30-31 )。
1950 年代初期,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筹建工作与全国社科院系大调整
同期展开,造就了一种共同的“马列主义民族学”流派(王建民、张海洋、
胡鸿保, 1998 : 67 )。进化论和唯物论无疑构成了这一“流派”的基础。这
时候的民族学学科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但也与此前
陶云逵等人所从事的民族学有了很大差别。
这种格局变动的结果,使“文化”被限制在国家学的框架之中,后者
是以“国家”作为全能主义的政治依据,而“社会”作为民主权力的政治依
据所形成的政治权力格局。“文化”及其表述均为这个框架所规定。这
似乎恰好映证了华勒斯坦( 1997 : 87 )的那句箴言:“社会科学一向是围绕
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对知识的生产往往发挥
着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提倡“世界体系”理论,意在追求超越国家。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超越国家的体系依然是个权力体系。由此,我们可
以说,在华勒斯坦的努力中,体现出的是一种超越与权力的两难困境。
陶云逵对文化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没有落入上述所谓的这种“华勒
斯坦困境”。他追求的是以历史文化为主体建立知识体系,追求“文化”
对政治的超越。从他的边政学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对“国家—
社会”的制约关系;从他对宗教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化”、“社
· 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