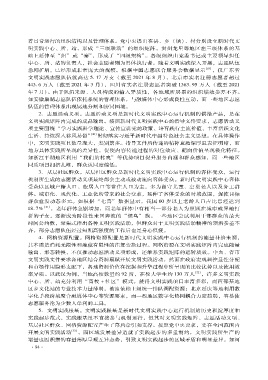Page 9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96
着日常运行的组织结构以及管理体系。党中央提出在县、乡 (镇)、村分别设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形成 “三级联动”的组织矩阵。贵州龙里等地区在三级体系的基
础上延伸至 “组”或 “寨”,形成了 “四级架构”。各级组织由党委书记或主要领导担任
中心、所、站的负责人,社会志愿者则为具体执行者。随着文明实践深入开展,志愿队伍
急剧扩增,已经形成非常庞大的规模。根据中国志愿联合服务会数据显示 ,仅广东省
〔 19〕
文明实践志愿队伍就高达 5. 17 万支 (截至 2021 年 8 月),北京市实名注册志愿者超过
443. 6 万人 (截至 2021 年 3 月),四川省实名注册志愿者突破 1363. 95 万人 (截至 2021
年 7 月)。由于队伍来源、人员构成的输入异质性,各地域所层累的组织绩效参差不齐。
如安徽巢湖志愿队伍依托系统的管理体系,与融媒体中心形成良性互动,而一些地区志愿
队伍的管理体系出现属地分割和协同困境。
2. 志愿活动义项。志愿活动义项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供给产品,是在
文明实践矩阵内完成的成品输出。按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指导文件要求,志愿活动义
项主要围绕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
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具体操作
〔 20〕
中,文明实践项目数量庞大,类别繁多。指导文件所传递的精神意蕴深厚且表征明晰,而
地方具体实践所呈现的差异性,促使内容传递过程的对位效应、靶向价值呈现极化特征。
如浙江平湖地区利用 “我们的村晚”等优势项目提升服务内涵和群众感知,而一些地区
同质项目拥挤扎堆,群众认同度偏低。
3. 基层社区群众。基层社区群众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客体受众,运行
机制所生成的志愿活动义项最终都会主动或被动流向客体受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客体
受众以区域户籍人口、旅居人口等常住人口为主,多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以及务工群
体。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延伸了客体受众的时域范围,促使目标
群众愈发动态多元。如根据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
18. 7% ,老年群体急剧增加,而老年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老人为照顾在城市或异地打
〔 21〕
拼的子女,逐渐成为阶段性来回奔波的 “候鸟”族。一些地区尝试利用干部群众的最大
时间公约数,聚集式推出各种文明实践活动,但群众对于文明实践活动精神的领悟参差不
齐,部分志愿队伍经过短期高强度的工作后也是身心俱疲。
4. 网格资源配置。网格资源配置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能量补给来源,
其本质是消耗无限性和蕴藏有限性的往复变换过程。网格资源在文明实践矩阵内完成能量
输出、形态转换,不仅推动志愿活动义项形成,还维系实践矩阵的运转质效。中央、省市
文明实践文件要求各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然而在政府宏观调控显性分配
和市场作用隐形支配下,各地资源价值在挖掘和升华过程中所呈现的比较优势以及使用效
率异质。以武汉为例,当地高校数量约 92 所,在校大学生约 130 万人 ,许多文明实践
〔 22〕
中心、所、站充分利用 “高校 +社区”模式,使得文明实践项目丰富多彩,而西部某地
区乡文化站的专业技术力量薄弱,被迫依赖上级统一排队调配资源;北京延庆等地利用数
字化手段跨域聚合融媒体中心等资源要素,而一些地区数字化协同耦合力度趋弱,容易使
志愿服务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
5. 文明实践根基。文明实践根基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运行机制的历史积淀厚度和
实践起步范式,实践根基虽不直接参与机制运行,但其对文明实践矩阵、志愿活动义项、
基层社区群众、网格资源配置产生了幕后牵引和支撑。按照党中央要求,要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 ,而区域发展差异造就了实践起步的多重制约,文明实践所生产的
〔 23〕
增量也因积攒的存量薄厚呈现互异态势,引致文明实践起步的区域矛盾和明显差异。如河
4 ·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