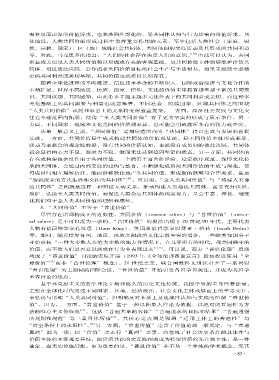Page 84 - 《党政研究》2021年第6期
P. 84
需要层面出发的价值诉求,也关涉到外部化的、受共同体认知与行为影响的价值诉求。具
体地说,人类共同价值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元素,至少包括人类社会 (家庭、民
族、宗教、国家)、区 (地)域性社会共同体、共同体间的交往活动及其形成的共同利益
等。对此,马克思多次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由此可以认为,共同
〔 9〕
利益或关切是人类共同价值赖以形成或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共同价值主体能够维护价值共
同体、增进彼此认同、合作追求共同价值目标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根基,如果未能建立起稳
定的共同利益或关切基础,共同价值也就难以长期存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国际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的
不断扩展,世界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信仰、文化的价值主体拥有越来越丰富的共同资
讯、共同议题、共同感知,由此带来了越来越多元化外表下的共同利益或关切。而这种多
元化基础上的共同需要与利益也就意味着,不同社会、民族国家、区域共同体之间围绕
“人类共同价值”认同和取舍上的关系将变得愈益复杂。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交
往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使得 “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了更为坚实的形成与展示条件,另一
方面,不同国家、地域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可能会引致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冲突。
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共同价值”是相应范围内的 “共同体”得以生成与发展的前提
基础。一方面,共同价值是生成或构建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是不同价值主体形成联系、
联动乃至联合的观念性前提,没有共同的价值认知,也就没有成员间的彼此认同,共同体
就会显得向心力不足、凝聚力不强,继而无法达到稳固坚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共同体的
存在或构建也会反作用于共同价值,一个拥有丰富合作经验、稳定秩序规范、深厚文化传
承的共同体,会通过内部交往的建构与整合,不断强化成员间共同价值的生成与深化,使
得成员间相互理解信任,继而潜移默化地产生共同价值,形成新的默契与合作关系,甚至
“造就按新的方式生活和交往的共同体” 。可以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与 “构建人类命
〔 10〕
运共同体”之间就是这样一种辩证互动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充分认识、
维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努力,又会丰富、深化、制度
化我们对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和感知。
3. “共同价值”不等于 “普世价值”
尽管存在语词构成上的近似性,共同价值 ( common values)与 “普世价值”( univer
sal values)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普世价值”的提法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代表
人物有德国神学家孔汉思 ( Hans Küng)、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 ( Isaiah Berlin)
等。那时,随着世界各国、地区、民族之间政治文化宗教冲突的增多,一些欧美知识分子
开始宣扬 “一种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代,都共同操守的
价值,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可以说,西方 “普世伦理”思潮
〔 11〕
构成了 “普世价值”讨论的实际开端 ( 1993 年 《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最初提议使用 “全
球价值” 而非 “普世伦理”概念)。21 世纪之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以
〔 12〕
“普世伦理”为主题词的国际会议,“普世价值”开始引发各国学界关注,并成为我国学
术界讨论的热点。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立场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学界的主导性看法是,
主张在全球化时代通过不同国家、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主体或层面上的平等交往,
来弘扬与形塑 “人类共同价值”,但明确反对本质上是地域性认知与实践的所谓 “普世价
值”。因为,一方面,“普世价值”基于一种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以绝对的普遍性为方
法的唯心主义价值观 ,包括 “普遍共享的客体”“普遍追求的目标和结果”“普遍遵循
〔 13〕
的规则和规范”等三重具体所指 ,其核心之点则是强调 “适用主体上的普遍性”与
〔 14〕
“时空条件上的永恒性”。 另一方面,“普世价值”违背了价值论的一般规定,与 “普遍
〔 15〕
真理”混为一谈,以 “价值”之衣行 “真理”之事,而忽视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性与
价值主体的主客观差异性,把价值共识的交互性扭曲成为特定价值的先在独立性,是一种
抽象、虚无的价值幻想。更为重要的是,“普世价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概念。究其
3 ·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