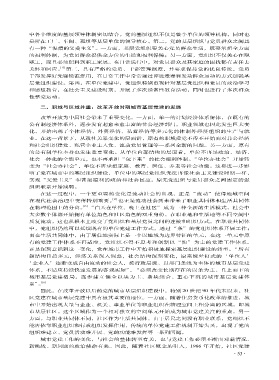Page 54 - 《党政研究》2021年第2期
P. 54
中各个维度的基层领导体制密切结合。党的基层组织不仅是整个单位的领导机构,同时也
是所在工厂、车间、班组等基层单位的领导核心。第二,党的基层组织与党员群众之间具
有一种 “温情的父爱主义”。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关心党员群众生活,既要承担全方面
的福利体制,为党员群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和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党组织不仅关心在职
职工,而且必须照料到职工家属。在日常运行中,对党员群众及其家庭的困扰都有责任去
关怀和回应。 第三,具有严格的党员、干部管理制度,并要求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员
〔 13〕
干部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通过评比竞赛和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第四,在单位党建中,党组织特别重视针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学习
和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了多次经常性教育活动,同时也进行了多次群众
性整党运动。
二、职域与区域并重: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基层党建的发展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单一的计划经济体系解体,在既有的
公有制经济体系外,逐步发育起愈来愈丰富的非公经济部门。职业领域也因此发生巨大变
化,开始出现了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等多元化的体制外经济组织的生产与就
业。在这一背景下,从政社关系变化的层面讲,原有的职域建党不得不开始面对非公经济
和社会组织建党、私营企业主入党、流动党员管理等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原有
的公有制单位本身也发生重要变化。从单位内部结构的层面看,单位不再是政治、经济、
社会一体化的全能单元,也不再承担 “包下来”的社会福利体制。“单位办社会”开始转
变为 “社会办社会”,单位不再承担家庭、教育、居住、养老等社会功能。这都进一步影
响了党在城市中的基层组织建设,单位中的基层党组织无法再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样,
实现 “父爱主义”和普遍福利的政治和社会回应,原先党组织与党员群众之间固定的强
组织联系开始减弱。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流动社会的出现,正是 “流动”使得地域空间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变得特别重要。 也正是流动社会到来带来了职业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
〔 14〕
在物理范围上的分离。 “白天在单位、晚上在社区”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社会中
〔 15〕
大多数个体都开始拥有单位角色和社区角色的双重身份,在职业地和生活地等不同空间中
反复流动,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组织和基层党员之间的连接和组织方式。在职业共同体
中,党组织仍然可以延续既有的单位党建工作方式,通过 “条”的党组织体系开展工作;
而在生活共同体中,由于居住地实际上是一个以地域为边界特征的单元,在这一单元中原
有的党建工作体系不再适应,党组织不得不思考和创新以 “块”为主的党建工作体系。
正是深刻意识到这一变化,党在城市工作中开始积极地探索基层组织建设的转型。“所有
制结构日趋多元,经济关系深入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原来螺丝钉式的 ‘单位人’
‘企业人’逐渐变成自由流动的社会人,按行政层级、以部门条线为主体的城市基层党建
体系,不适应持续快速发展的客观实际”,“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以条为主、自上而下的
城市基层党建格局,逐步建立健全以块为主、条块结合、重心下沉的城市基层党建体
系”。
〔 16〕
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党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中,特别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社
区党建在城市基层党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推进,城
市中开始出现大量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职业组织在物理空间上相分离的区域,即城
市基层社区。这个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开始成为城市党建关注的重点。另一
方面,与职业共同体不同,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由于居民之间没有职业联系,党组织不
能再依靠职业组织和行政组织发挥作用,传统的单位党建工作机制开始失灵,出现了党的
组织难建立、党员活动难开展、党的功能难发挥等一系列问题。
城市党建工作的变化,与社会的整体转型有关,也与党建工作必须不断面对新情况、
新挑战、新问题的政治使命有关。因此,随着社区概念的引入,1986 年开始,社区党建
3 ·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