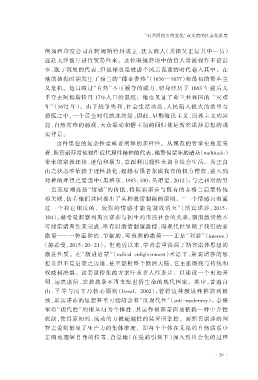Page 36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36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例如西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成立,犹太商人(其祖父正是其中一员)
远赴大洋彼岸进行贸易往来。 这位眼镜磨坊中的哲人常被视作不谙世
事、耽于沉思的代表,但他却总是被那个风云诡谲的时代卷入其中。 在
他的孩提时期发生了荷兰的“郁金香热”( 1636—1637)和最初的资本主
义危机。 他目睹过“自然”不可褫夺的威力,切身经历了 1663 年前后几
乎夺去阿姆斯特丹 17%人口的鼠疫; 他也见证了荷兰共和国的“灾难
年”(1672 年)。 由于战争失利,社会生活动荡,人民陷入极大的绝望与
恐慌之中,一个黄金时代就此终结。因此,早期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兴
起,自然灾难的涌现,大众暴动和僭主制的回归都是斯宾诺莎思想的现
实背景。
这种思想的复杂性意味着阐释的多样性。 从规范的哲学史角度来
看,斯宾诺莎常被视作近代理性精神的代表。他警惕蒙昧的诸众( multitude)
带来的宗教狂热、迷信和暴力,意图利用理性来调节社会生活。 真正自
由之状态唯依赖于理性教化,超越有限者尔虞我诈的权力博弈,进入到
对神的理智之爱当中(黑格尔,1983:100;吴增定,2012);与之相对的另
一重态度则高扬“情感”的价值,将斯宾诺莎与既有的苏格兰启蒙传统
相关联,仿若他们共同提出了某种激情制衡的原则。“一个情感只有通
过一个和它相反的, 较强的情感才能 克 制或消 灭 ”(斯宾 诺 莎 ,2015:
104)。赫希曼洞察到斯宾诺莎与初生的市民社会的关联。驯服激情绝不
可能借诸理性来完成,唯有以激情制服激情,而现代世界赋予我们的新
激情———一种温和的、节制的、可预测的激情———正是“利益”(interest)
(赫希曼,2015:20-21)。 但晚近以来,学者着重强调了斯宾诺莎思想的
激进性质。 在“激进启蒙”(radical enlightenment)术语下,斯宾诺莎的思
想非但不是启蒙之边缘,甚至辐射整个欧洲大陆。 它主张彻底与传统和
权威相决裂。 这套世俗化的方案吁求着人性进步, 以建设一个更加开
明、远离迷信、宗教教条不再支配世俗生命的现代国家。 其中,普遍自
由 、平 等 与 民 主乃 核 心 原 则(Isreal, 2002);若 将 这 种 激 进 性 推 演 到极
致,斯宾诺莎的思想甚至可能暗含着“反现代性”(anti-modernity)。 奈格
里将“现代性”的根基归为个体性,其运作根深蒂固地依赖一种中介性
机制,使得原初的、流动的力被超越性的装置所掌控。 而斯宾诺莎的理
智之爱则彰显了生产力的集体维度, 即每个个体在无限的自然联系中
正确地理解自身的位置,自觉地(在爱的引领下)加入到社会化的过程
·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