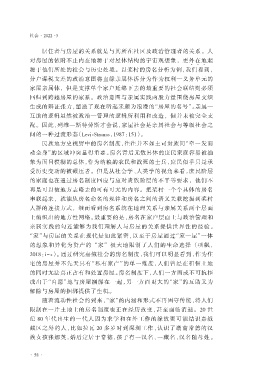Page 65 - 《社会》2022年第3期
P. 65
社会·2022·3
居住者与房屋的关系就是与其所在社区及政治管理者的关系。 人
对房屋的依附不止内在地源于对屋体结构的宇宙观想象, 更N在地起
外在·
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与历史处境。 以桨村的房名分析为例,我们看到,
分户课税支差的政治意图将血缘亲属体拆分为作为权利—义务单元的
家屋亲属体, 但是支撑单个家户延绵下去的最重要的社会联结则必须
回归到跨越房屋的家系。 政治意图与亲属实践两股力量围绕房屋交织
生成的辩证张力,塑造了现在听起来颇为浪漫的“房屋的名号”。亲属—
互助的逻辑虽然被政治—管理的逻辑所利用和改造, 但并未被完全支
配。 因此,列维—斯特劳斯才会说,家屋社会是亲属社会与等级社会之
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Levi鄄Strauss,1987:151)。
民族地方史视野中的房名制度,往往并不如土司贵族间“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区域冲突显得重要。 房名背后无数具体的庶民家庭容易被抽
象为面目模糊的总体,作为纳粮的农民和战死的士兵,庶民似乎只是承
受历史变动的被碾压者。 但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庶民阶层
的家庭也在通过房名制度回应与应对贵族阶层的不平等要求, 他们不
再是可以被地方志略去的可有可无的内容。 把桨村一个个具体的房名
串联起来, 就能从房名命名的规律和房名之间的语义关联挖掘到桨村
人群的连接方式, 继而看到房名系统在地理关系与亲属关系两个层面
上编织出的地方性网络。 最重要的是,房名在家户层面上与政治管理和
亲属实践的勾连能够为我们理解人与房屋的关系提供世界性的经验。
“家”与房屋的关系在现代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房屋通过“家—屋”一体
的想象和异化为资产的“家” 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生命选择 (项飙,
2018:i-x)。 通过研究嘉绒社会的房名制度,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作为住
宅的房屋并不先天具有“私有家产”的单一维度,人们曾经在租佃土地
的同时无法真正占有和处置房屋。 房名制度下,人们一方面或不可抗拒
或出于“自愿”地与房屋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更大的“家”的互助又为
解除与房屋的捆绑提供了生机。
随着流动性社会的到来,“家”的内涵和形式不再固守传统,将人们
限制在一片土地上的房名制度也正在经历改变,甚至面临消逝。 20 世
纪 8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因为求学和在N工作的缘故更可能结识嘉绒
藏区之N的人,比如拉瓦 20 多岁时到深圳工作,认识了湖南常德的汉
族女孩张娜英,婚后定居于常德,孩子有一汉名、一藏名,汉名随母姓。
外 58 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