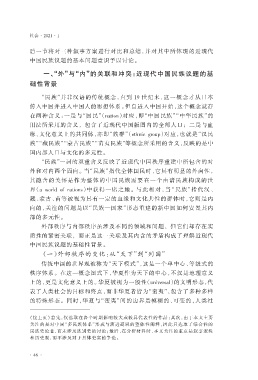Page 53 - 《社会》2021年第1期
P. 53
社会·2021·1
后一节将对三种叙事方案进行对比和总结,并对其中所体现的近现代
中国民族议题的基本问题意识予以讨论。
一、“外”与“内”的关联和冲突:近现代中国民族议题的基
础性背景
“民族”并非汉语的传统概念,直到 19 世纪末,这一概念才从日本
传入中国并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但自进入中国开始,这个概念就存
在两种含义:一是与“国民”( nation)对应,即“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
用法所采用的含义, 包含了近现代中国版图内的全部人口; 二是与血
缘、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亦即“族群”(ethnic group)对应,也就是“汉民
族”“藏民族”“蒙古民族”“苗夷民族”等概念所采用的含义,反映的是中
国内部人口与文化的多元性。
“民族”一词的双重含义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秩序重建中所包含的对
外和对内两个面向。 当“民族”指代全体国民时,它具有明显的外向性,
其隐含的关怀是作为整体的中国民族需 要在一个由诸 民族构 成的世
界( a world of nations)中获得一席之地。 与此相 对,当“民族”指 代汉 、
藏、蒙古、苗等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血缘和文化共性的群体时,它则是内
向的,关注的问题是以“民族—国家”形态重建的新中国如何安置其内
部的多元性。
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虽涉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 但它们却存在实
质性的紧密关联, 而正是这一关联及其内含的矛盾构成了理解近现代
中国民族议题的基础性背景。
(一)外部秩序的变化:从“天下”到“列国”
传统中国的世界观被称为“天下模式”,这是一个单中心、等级式的
秩序体系。 在这一概念图式下,华夏作为天下的中心,不仅是地理意义
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 华夏被视为一般性(universal)的文明形态,代
表了人类社会的目标和终点,而非华夏者皆为“蛮夷”,包含了多种多样
的特殊形态。 同时,华夏与“蛮夷”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可变的,人类社
(接上页)首先,仅选取在各个时期影响较大或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其次,由于本文主要
关注的是对中国“多民族体系”形成与演进逻辑的整体性阐释,因此只选取了综合性的
民族史论著,而未涉及族别史的讨论;最后,在分析材料时,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叙事逻辑
和历史观,而不涉及对于具体史实的争论。
·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