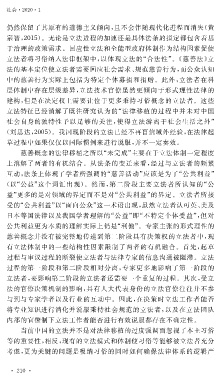Page 217 - 《社会》2020年第1期
P. 217
社会 · 2020 · 1
仍然保留了其原有的道德主义倾向 , 且不会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消失 ( 黄
宗智 , 2015 )。 无论是立法进程的加速还是具体法条的拟定都包含着基
于治理的政策需求 。 回应性立法和全能型政府体制作为结构因素促使
立法者将习俗纳入法律框架中 , 以体现立法的 “ 合法性 ”。《 慈善法 》 立
法的基本定位使立法者需要回应社会需求 、 规范慈善行为 , 而公众认知
中的慈善行为实际上包括为特定个体募捐和捐赠 。 此外 , 立法者在科
层体制中存在层级差异 , 立法技术官僚虽然更倾向于形式理性法律的
建构 , 但是在决定权上需要让位于更多秉持习俗概念的立法者 。 这些
立法特征已经消解了既往研究认为的 “ 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并未对中国
社会自身的独特性予以足够的关注 , 使得立法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 ”
( 刘思达 , 2005 )。 我国现阶段的立法已经不再盲信域外经验 , 在法律起
草过程中如果仅仅以国际惯例来进行说服 , 并不一定奏效 。
慈善概念的法律移植之所以 “ 未完成 ” 主要在于立法体制一定程度
上消解了两者的有机结合 。 从法条的变迁来看 , 经过与立法者的频繁
互动 , 法条上体现了学者所强调的 “ 慈善活动 ” 应该是为了 “ 公共利益 ”
( 以 “ 公益 ” 这个词汇出现 )。 然而 , 第二阶段主要立法者所认知的 “ 公
益 ” 更多的是对领域的界定而不是对 “ 公共利益 ” 的界定 。 立法者所接
受的 “ 公共利益 ” 以 “ 面向公众 ” 这一术语出现 , 虽然立法者认可英 、 美及
日本等国法律以及我国学者理解的 “ 公益 ” 即 “ 不特定个体受益 ”, 但对
公共利益更为本质的理解实际上仍是 “ 利他 ”。 专家主张的形式理性的
慈善概念并没有被完整地传递到第二阶段具有决策权的立法者中 , 现
有立法体制中的一些结构性因素限制了两者的有机融合 。 首先 , 起草
过程与审议过程的断裂使立法者与法律专家的信息沟通被阻滞 。 立法
过程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相对分离 , 专家更多地影响了第一阶段的
立法者 , 要影响第二阶段的立法者还需要一个重复的过程 。 其次 , 受立
法的官僚决策机制的影响 , 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立法官僚往往并不参
与到与专家学者以及行业的互动中 。 因此 , 在决策时立法工作者能否
将专业知识进行消化并说服秉持社会规范的立法者 , 以及在立法团队
内部的官僚制下立法工作者能否进行有效说服都存在不确定性 。
当前中国的立法并不是对法律移植的过度强调而忽视了本土习俗
等的重要性 , 相反 , 现有的立法模式和体制使习俗等能够被立法者充分
考虑 ,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吸纳习俗的同时如何确保法律体系的逻辑严
0
· 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