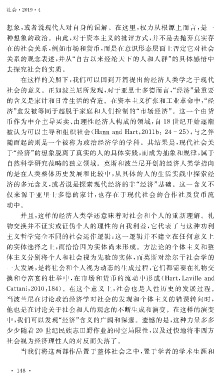Page 155 - 《社会》2019年第4期
P. 155
社会· 2019 · 4
想象,或者说现代人对自身的误解。在这里,权力从根源上而言,是一
种想象的政治。由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方式,并不是去抛弃真实存
在的社会关系,例如市场和货币,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否定它对社会
关系的观念表述,并从“自古以来经纶天下的人和人群”的具体感悟中
去探究社会的实质。
在这样的关照下,我们可以回到开篇提出的经济人类学之于现代
社会的意义。正如波兰尼所发现,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经济”最重要
的含义是家计和日常生活的营造。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业革命中,“经
济”愈发被等同于超脱于家庭和人们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个由货
币作为中介主导买卖、由理性经济人构成的领域,自 18 世纪开始逐渐
被认为可以主导和组织社会( 犎犪狀狀犪狀犱犎犪狉狋 , 2011犫 : 24-25 ),与之伴
随而起的则是一个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其结果是,现代社会关
于“经济”的想象脱离了真实的人的具体实践,而成为抽象和规律,属于
自然科学研究范畴的独立领域。莫斯和波兰尼开创的经济人类学指向
的是在人类整体历史发展和比较中,从具体的人的生活实践中探索经
济的多元含义,或者说是探索现代经济的非“经济”基础。这一含义不
仅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家计,也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合作社及货币流
动中。
并且,这样的经济人类学还意味着对社会和个人的重新理解。礼
物交换并不证实或证伪个人的理性的自我利益,它代表了与这种功利
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社会运作逻辑:这一逻辑并不建立在任何意义上
的实体选择之上,而恰恰因为实体尚未形成。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
体主义分别将个人和社会视为先验的实体,而莫斯对涂尔干社会学的
一大发展,是将社会和个人视为动态的生成过程,它们都需要在礼物交
换和夸富宴的壮举中,在市场和货币的流动中形成( 犎犪狉狋 , 犔犪狏犻犾犾犲犪狀犱
犆犪狋狋犪狀犻 , 2010 : 184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也是人性历史的发展过程。
当波兰尼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的发现和个体主义的错误转向时,
他也是在讨论关于社会和人的观念的不断生成和演变。在这样的演变
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含义的广阔和深邃。遗憾的是,这种力量多多
少少随着 20 世纪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时空局限性,以及过快地将非西方
社会视为经济理性人的对反而失落了。
当我们将这两部作品置于整体社会之中,置于学者的学术生涯和
· 1 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