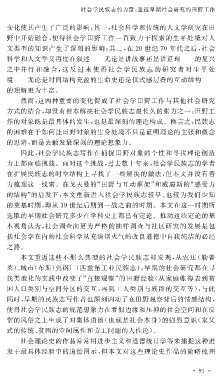Page 98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98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变化使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一,社会科学和传统的人文学研究在田
野中开始融合,使得社会学田野工作一直致力于探索的生平处境对人
文类型的知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社会
科学和人文学又再度在叙述———无论是讲故事还是讲道理———的复兴
之中并行 和 融 合,这 反 过 来 使 得 社 会 学 民 族 志 的 研 究 者 对 生 平 处
境———无论是时间结构充盈的生命史还是仪式感层叠的互动结构———
的理解更为丰富。
然而,这两种重要的变化促成了社会学田野工作与其他社会研究
方式的结合,却没有根本解决社会学民族志最长久的张力之一:田野工
作的对象既是最具体的发生,也是最深刻的理论构成。换言之,民族志
的困难在于如何让田野对象的生身处境不只是证明理论的主张和概念
的思辨,而是去触发最深刻的理论想象力。
因此,社会学民族志写作在捕捉田野对象的个性和寻找理论创造
力上都面临挑战。面对这个挑战,过去数十年来,社会学民族志的学者
在扩展民族志的时空结构上寻找了一些解决的做法,但本文并没有着
力梳理这一线索。在戈夫曼的“田野与互动框架”和威廉斯的“感受力
的结构”的启发下,本文重新进入社会学民族志较早、也较为我们少知
的奠基时期,即从 19 世纪后期到一战之前的时期。本文在这一时期所
选取的早期社会研究多少在学科史上都已有定论。推动这些定论的基
本视角认为,社会调查向更为严格的抽样调查与社区研究的发展是包
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从充满烟火气的改良道德中自我纯洁的必经
之路。
本文重返这些不那么典型的社会学民族志却发现,从农庄(勒普
莱)、城市(布斯)到钢厂(匹兹堡工业民族志),早期的社会研究都在寻
找类型化的实践中改变了“直接观察”的田野经验(从家庭账簿表到贫
困人口类别与空间分区的交互,再到工人类别与族群的交互等),与此
同时,早期的民族志写作者也深刻调动了在田野观察背后的情感结构,
使得社会学民族志的规范想象力在看似边缘和压抑的社会空间和在反
常的风俗之上生成了对集体道德(也就是社会本身)的强烈意识(家父
式的传统、贫困的空间属性和劳工问题的人性论)。
社会理论史的作品常常用进步主义和道德统计学等来捕捉这种迸
发于最具体经验中的道德图示,但本文对这些理论史作品的简略梳理
· 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