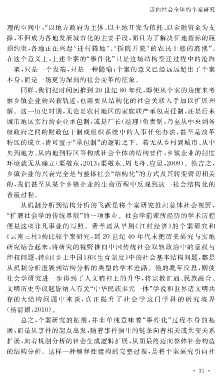Page 38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38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理的空间中,“以地方政府为主体、以土地开发为依托、以金融资金为支
撑,不但成为各地发展城市化的主要手段,而且为了解决征地指标的瓶
颈约束,各地正在兴起‘迁村腾地’、‘拆院并院’的农民上楼的高潮”。
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个案的“事件化”只是这场结构变迁过程中的沧海
一粟,只是一个发端,只是一种隐喻;个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个案
本身,而是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征象。
同样,我们把时间回推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即便从个案的角度来考
察乡镇企业的兴衰轨迹,也需要从结构化的社会关联入手加以扩展理
解。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后来
城市地区实行的企业承包制,或是厂长(经理)负责制,乃至从中央到各
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包干制或组织系统中的人事任免办法,甚至是改革
特区的成立,皆可置于“承包制”的逻辑之下。若无从乡村到城市、从中
央到地方、从内地到特区等构成社会全体的结构要件,乡镇企业的制度
环境就无从确立(渠敬东, 2013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2009 )。换言之,
乡镇企业的兴衰完全是与整体社会“结构化”的方式及其转变密切相关
的,我们甚至从某个乡镇企业的生命历程中反观到这一社会结构化的
普遍过程。
从机制分析到结构分析的飞跃是将个案研究推向总体社会视野,
“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一项事业。社会学前辈所经历的学术历程
便是这项非凡事业的写照。费孝通从早期《江村经济》的个案研究和
《云南三村》的比较个案研究,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把历史研究与实地
研究结合起来,将研究的视野推向中国传统社会双轨政治中的皇权与
绅权问题,转向《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中的社会基本结构问题,都是
从机制分析进展到结构分析的典型的学术进路。他的晚年反思,则使
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得到了人文精神上的升华,将宗教汇通、民族融合、
文明历史等议题皆纳入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和世界诸文明共
存的大结 构 问 题 中 来 谈,真 正 提 升 了 社 会 学 这 门 学 科 的 研 究 境 界
(杨清媚, 2010 )。
总之,个案研究的拓展,并非单纯意味着“事件化”过程本身的拓
展,而是从事件的起点出发,随着事件演生的链条向着相关或共变关系
扩展,向着机制分析的社会生成逻辑扩展,从而最终迈向整体社会构造
的结构分析。这样一种解释性建构的完整过程,是将个案研究引向社
· 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