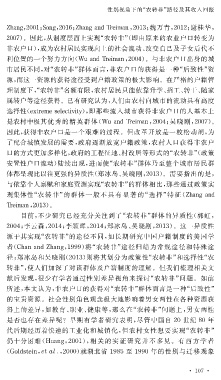Page 114 - 《社会》2018年第3期
P. 114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
,
犣犺犪狀 犵2001 ; 犛狅狀 犵2016 ; 犣犺犪狀 犵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2013 ;魏万青, 2012 ;谢桂华,
2007 )。因此,从制度层面上实现“农转非”(即由原来的农业户口转变为
非农户口),成为农村居民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改变自己及子女后代不
利位置的一个努力方向(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2004 )。与非农户口出身的城
市居民不同,对“农转非”群体而言,非农户口的获得是一种“后致性”资
源,而这一资源的获得途径受到户籍政策的极大影响。在严格的户籍管
理制度下,“农转非”名额有限,农村居民只能依靠升学、招工、转干、随家
属转户等途径获得。已有研究认为,人们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具有高度
选择性( 犲狓狋狉犲犿犲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犻狋 狔 ),即那些流入城市获得非农户口的人基本上
是农村中极其优秀的精英群体( 犠狌犪狀犱犜狉犲犻犿犪狀 , 2004 ;吴晓刚, 2007 )。
因此,获得非农户口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改革开放是一枚松动剂,为
了配合城镇发展的需要,政府逐渐放宽户籍政策,农村人口获得非农户
口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政府的工程征地、村改居等形式的“农转非”(政策
安置性户口流动)陆续出现,进而使“农转非”群体乃至整个城市居民群
体都呈现比以往更强的异质性(郑冰岛、吴晓刚, 2013 )。需要指出的是,
与依靠个人禀赋和家庭资源实现“农转非”的群体相比,那些通过政策实
现集体性“农 转 非”的 群 体一 般不 具 有 显 著 的“选 择”特 征( 犣犺犪狀 犵犪狀犱
犜狉犲犻犿犪狀 , 2013 )。
目前,不少研究已经充分关注到了“农转非”群体的异质性(郭虹,
2004 ;李云森, 2014 ;李颖晖, 2014 ;郑冰岛、吴晓刚, 2013 )。这一异质性
源于其实现“农转非”的途径不同,如长期研究中国户籍制度的美国学
者( 犆犺犪狀犪狀犱犣犺犪狀 犵1999 )将“农转非”途径归结为常规途径和特殊途
,
径;郑冰岛和吴晓刚( 2013 )则将其划分为政策性“农转非”和选择性“农
转非”,使人们加深了对该群体及户籍制度的理解。但我们梳理相关文
献后发现,很少有学者通过性别差异视角来探讨“农转非”问题。如前
所述,本文认为,非农户口的获得对“农转非”群体而言是一种“后致性”
的宝贵资源。社会性别角色观念极大地影响着男女两性在各种资源获
得上的差异,如教育、职业、健康等,那么在“农转非”问题上,男女两性
是否也存在差异呢?早期有学者研究表明,尽管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期经历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农村女性想要实现“农转非”
,
仍十分困难 ( 犎狌犪狀 犵 2001 ),相关 的 实证 研究 并不多见。有西方学 者
( 犌狅犾犱狊狋犲犻狀 , 犲狋犪犾. , 2000 )就湖北省 1985 至 1990 年的性别与迁移现象
· 1 0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