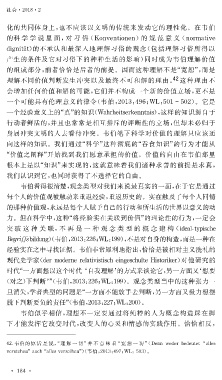Page 191 - 《社会》2018年第2期
P. 191
社会· 2018 · 2
化的共同体身上,也不应该以文明的传统来发动它的理性化。在韦伯
的科 学 学 说 里 面,对 习 俗 ( 犓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犲狀 )的 规 范 意 义 ( 狀狅狉犿犪狋犻狏犲
犱犻 犵 狀犻狋狋 )的不承认和最深入地理解习俗的观念(包括理解习俗所得以
产生的条件及它对习俗下的种种生活的影响)同时成为韦伯理解价值
的组成部分,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前提。因而这种理解不是“宽恕”,而是
理解不同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以及最终不可和解的理由。 42 这种理由不
会增加任何价值和解的可能,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新的价值立场,更不是
一个可能具有伦理意义的律令(韦伯, 2013 : 496 ; 犠犔 : 501-502 )。它是
一个经验意义上的“真”的知识( 犠犪犺狉犺犲犻狋狊犲狉犽犲狀狀狋狀犻狊 ),这样的知识源自于
行动者鲜活的,并且也常常是相互排斥的评断性的立场,但却未必归于
身属冲突文明的人去看待冲突。韦伯笔下科学对价值的理解只应该通
向这样的知识。我们通过“科学”这种彻底的“吞食知识”的行为才能从
“价值之阐释”开始找到我们愿意承担的价值。价值的自由在韦伯那里
根本上是以“知识”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诸种求善的前提是求真,
我们认识到它,也同时获得了不选择它的自由。
韦伯看得很清楚,观念类型对我们来说最真实的一面,在于它是通过
每个人的价值观被触动来重返经验,重返历史的。实在触及了每个人同情
的那种价值观,永远是每个人赋予自己的行动和所生活的世界以意义的动
力。但在科学中,这种“将经验实在关联到价值”的理论性的行为,一定会
突 破 这 种 关 联,不 再 是 一 种 观 念 类 型 的 概 念 建 构 ( 犻犱犲犪犾狋 狔狆 犻狊犮犺犲
犅犲 犵 狉犻 犳犳 狊犫犻犾犱狌狀 犵 )(韦伯, 2013 : 226 ; 犠犔 : 199 ),不是对自身的构造,而是一种在
经验实在之中寻找证据。韦伯非常犀利地指出,恰恰是被相对主义洗礼的
现代史学家( 犱犲狉犿狅犱犲狉狀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犻狊狋犻狊犮犺犲犻狀 犵 犲狊犮犺狌犾狋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犽犲狉 )对他研究的
时代“一方面想以这个时代 ‘自我理解’的方式来谈论它,另一方面又‘想要
(对之)下判断’”(韦伯, 2013 : 226 ; 犠犔 : 199 )。观念类型当中的这种张力一
旦消失,学者典型的问题是“一方面不能放手去判断,另一方面又极力想摆
脱下判断要负的责任”(韦伯, 2013 : 227 ; 犠犔 : 200 )。
韦伯似乎相信,理想不一定要通过将纯粹的人为概念构造踩在脚
下才能发挥它改变时代,改变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实践作用。恰恰相反,
42. 韦伯的 原 话 是 说,“理 解 一 切 ”并 不 意 味 着 “宽 恕 一 切 ”( 犇犲狀狀 狑犲犱犲狉犫犲犱犲狌狋犲狋 “ 犪犾犾犲狊
狏犲狉狊狋犲犺犲狀 ” 犪狌犮犺 “ 犪犾犾犲狊狏犲狉狕犲犻犺犲狀 ”)(韦伯, 2013 : 497 ; 犠犔 : 503 )。
· 1 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