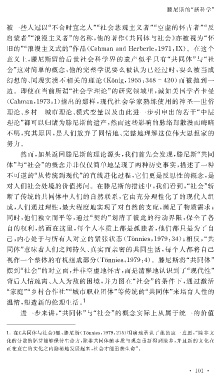Page 108 - 《社会》2016年第2期
P. 108
滕尼斯的“新科学”
被一些人冠以“不合时宜之人”“社会悲观主义者”“空虚的怀古者”“反
启蒙者”“浪漫主义者”的名称,他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亦被视为“怀
旧的”“浪漫主义式的”作品( 犆犪犺犿犪狀犪狀犱犎犲狉犫犲狉犾犲 , 1971 : 犐犡 )。在这个
意义上,滕尼斯留给后世社会科学界的遗产似乎只有“共同体”与“社
会”这对简单的概念,他的完整学说要么被认为已经过时,要么被当成
,
幻想的、同现实漠不相关的理论( 犓狀犻 犵1955 : 348-420 )而被抛到一
边。即使在当前所谓“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领域里,诚如美国学者卡曼
( 犆犪犺犿犪狀 , 1973 : 1 )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学家熟练使用的神圣—世俗
理论、乡村—城市理论、模式变量以及由此进一步引申出的若干“中层
理论”都可以归诸为滕尼斯的遗产,然而这些影响的脉络却散漫而晦暗
不明,究其原因,是人们放弃了同情地、完整地理解这位伟大思想家的
努力。
然而,如果返回滕尼斯的理论源头,我们首先会发现,滕尼斯“共同
体”与“社会”的概念并非仅仅简单地呈现了两种历史事实,描述了一种
不可逆的“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进化过程,它们更是反思性的概念,是
对人们社会处境的价值拷问。在滕尼斯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社会”斩
断了传统的共同体中人们的自然联系,它由充分理性化了的现代人组
成,人们通过理性,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自然的支配,满足了物质需求;
同时,他们独立而平等,通过“契约”划清了彼此的行动界限,保全了各
自的权利,然而在这里,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孤独者,他们都只是为了自
己,内心处于与所有人对立的紧张状态( 犜狀狀犻犲狊 , 1979 : 34 );相反,“共
同体”意味着人们之间持久、真实而亲密的共同生活,每个人都将自己
视作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犜狀狀犻犲狊 , 1979 : 4 )。滕尼斯将“共同体”
摆到“社会”的对立面,并非空虚地怀古,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性”
背后人情疏离、人人为敌的困境,并力图在“社会”的条件下,通过激活
“家庭”“乡村合作社”“城市职业团体”等传统的“共同体”来培育人性的
温情,塑造新的伦理生活。 1
进一步来讲,“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实际上从属于统一的价值
1. 在《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1979 : 215 )明确地承认了他的这一意图,“除非文
化的分散的胚芽能够保持生命力,除非共同体的本质与观念重新得到滋养,并且新的文化在
正在衰亡的文化之内隐秘地发展起来,社会才能重获生命”。
· 1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