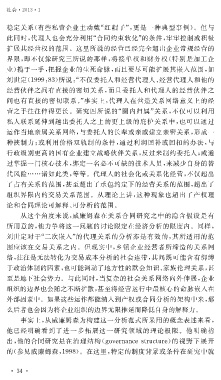Page 41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41
社会· 2013 · 1
稳定关系(有些私营企业主动戴“红帽子”,更是一种典型事例)。但与
此同时,代理人也会充分利用“合同约束软化”的条件,牢牢控制或积极
扩展其经营权的范围。这里所说的经营已经完全超出企业常规经营的
界限,即不仅像研究三所说的那样,将接单权和财务权(特别是加工企
业)揽于一手,把握企业的生死命脉,而且要尽可能扩展其嵌入范围,如
刘世定( 1999 : 83 )所说:“不仅委托人和经营代理人、经营代理人和他的
经营伙伴之间有直接的密切关系,而且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经营伙伴之
间也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事实上,代理人在营造关系网络意义上的经
营之手往往伸得更长。研究四所说的“圈内归属”关系,不仅可以利用
私人联系延伸到越出委托人之上的更上级的庇护关系中,也可以通过
运作当地亲属关系网络,与委托人的长辈或亲戚建立亲密关系,形成一
种挟制力;或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条件,通过利润回补或回扣的办法,与
行政级别更高的国有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反过来制约委托人;或通
过掌握一门核心技术,绑定一名必不可缺的技术人员,来减少自身的替
代风险……诸如此类,等等。代理人的社会化或关系化经营,不仅超出
了占有关系的范围,甚至超出了承包约定下的经营关系的范围,超出了
组织界限内的交易关系范围。从理论上讲,这种现象也超出了产权理
论和合同理论可解释、可分析的范围。
从这个角度来说,威廉姆森在关系合同研究之中的隐含假设是有
所用意的,他力争将这一问题的讨论限定在经济分析的限度内。同样,
刘世定对于“二次嵌入”的代理关系的分析亦是有效的,其所适用的范
围应该在交易关系之内。但现实中,乡镇企业经营者所缔造的关系网
络,往往是无法转化为交易成本分析的社会连带,其间既可能含有绑缚
于政治体制的因素,也可能调动了地方性的默会知识、家族伦理关系,甚
至是地下社会势力。与此同时,当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向外伸展,企业
组织的边界也会随之不断扩散,甚至将经营运行中最核心的命脉嵌入在
外部因素中。如果这些运作都能纳入到产权或合同分析的架构中来,那
么后者也会因为将企业组织的边界无限推延而降低自身的解释力。
事实上,从威廉姆森为构建这一分析范式所采用的概念表述来看,
他已经明确看到了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极限。他明确指
出,他的合同研究是在治理结构( 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的视野下展开
犵
的(参见威廉姆森, 1998 )。在这里,特定的制度背景或条件在研究中就
·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