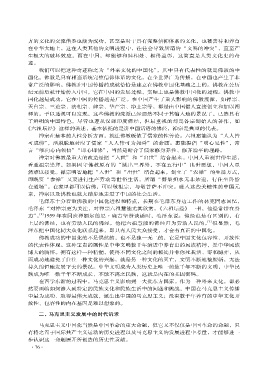Page 77 - 《党政研究》2021年第5期
P. 77
方的文化的交流借鉴也颇为成功,甚至是对于具有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也被善待和养育
在中华大地上,这在人类其他的文明进程中,往往会导致所谓的 “文明的冲突”,直至产
生极大的破坏效应,而在中国,却能够和睦相处、相得益彰,这简直是人类文化史的奇
迹。
我们可以把这种奇迹称之为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佛教的中
国化。佛教是具有相当系统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在中国也产生了非
常广泛的影响。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在公历
纪元前后就开始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
国化越是成功,它在中国的传播越是广泛。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流派,如禅宗、
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和加以阐
释的。予以透视可以发现,这些佛教的流派已经迥然不同于其输入地的景况了,已然具有
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也遵从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视的却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如
《六祖坛经》这样的著述,基本依托的是讲中国话语的佛经,禅宗是典型的代表。
禅宗在基本的人性分析方面,就让佛教皈依了儒家的性善论。六祖惠能认为 “人人皆
可成佛”,活脱脱地对应了儒家 “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命题。惠能提倡 “明心见性”,常
言 “唯向心内领悟”“即心即佛”,当然是暗合了儒家修身养性、修齐治平的理路。
禅宗对佛教最重大的改造是把 “入世”和 “出世”结合起来。中国人重视世俗生活,
看重祖宗崇拜,如果固守佛教原有的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世思想,中国人显
然难以接受。禅宗明智地把 “入世”和 “出世”结合起来,创立了 “农禅”的生活方式,
即既要 “参禅”又要进行生产劳动等世俗生活,所谓 “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
在道场”。在家里都可以信佛,可以敬祖宗,与敬菩萨不冲突。融入这些关键性的中国元
素,禅宗以及佛教也就大踏步地走进了中国的社会生活。
毛泽东十分看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特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同志回忆,
毛泽东 “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
边”。 1959 年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毛泽东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
〔 2〕
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把六祖慧能的佛经归为劳动人民的。 很显然,毛
〔 3〕
泽东把中国化同大众化联系起来,即只有人民大众接受,才会有真正的中国化。
佛教成功的中国化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中国文化包容性、开放性
的代表性体现。这种宝贵的属性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中养育出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
博大的胸怀。拥有这样一种精髓,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并非你死我活、零和博弈,从
而成功地避免了往往一种文化的兴起,就是另一种文化的灭亡,文明不断地被腰斩,无法
持久绵恒地发展下去的景况。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数千年不断的文明,中华民
族成为唯一数千年不断成长、不散不离之民族,这就是内在的基因密码。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到一大批东方国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都必
然要面临如何渗入到特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最为成功、取得最伟大成就,诞生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数千年养育的中华文化开
放性、包容性的内在基因是难以想象的。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时代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是中国革命的重大命题,但它又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命题,只
有将之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考量,才能够进一
步认识这一命题展开所创造的历史性贡献。
6 ·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