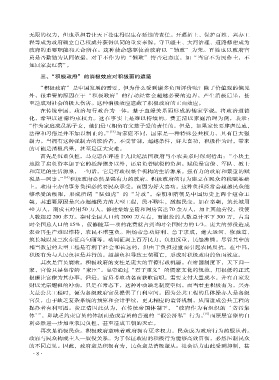Page 8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P. 8
无限的权力,但也承担着让天下苍生得以生存延续的责任。开疆拓土、保护百姓、兴办工
程等成为政府确立自己权威并获得认同的重要来源。守卫疆土、大河治理、道路修建成为
政府的重要职能和天命所在。这种使命感驱使着政府以 “勤政”为荣。百姓也以政府官
员是否勤勉为认同依据,对于不作为的 “懒政”持否定态度,如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
如回家卖红薯”。
三、“积极政府”的消极效应对积极面的遮蔽
“积极政府”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但为什么受到诸多负面评价呢?除了价值观的偏见
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积极政府”的行动经常会超越必要的边界,产生消极后果,甚
至造成对社会的极大伤害。这种消极效应遮蔽了积极政府的正面效应。
在传统中国,政治与行政合为一体。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儒家学说,将政治道德
化,希望以道德约束权力。这在事实上是难以持续的。费正清以家庭治理为例,表示:
“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他们是互相负有父慈子爱的责任的。但是,如果家长要肆虐逞威,
法律和习俗是并不加以制止的。” 与家庭不同,国家是一种特殊公共权力,具有巨大强
〔 13〕
制力。当拥有这种强制力的统治者,不受节制,超越条件,好大喜功,积极作为时,带来
的可能是消极后果,甚至是巨大灾难。
首先是沉重负担。马克思在评述十九世纪法国政府与小农关系时深刻指出:“小块土
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以外,还肩负着赋税的负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
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
税是一回事。” 积极政府必然是强有力的政府。积极政府的行为建立在民众的税赋基础
〔 14〕
上。政府主办的事务负担必然要民众承受。而因为好大喜功,这种负担经常会超越民众能
够承受的极限,形成所谓 “猛如虎”的 “苛政”。秦朝和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短命王
朝,其重要原因是兴办超越民力的大型工程,民不聊生,激起民变。如在秦朝,筑长城用
40 万人,南戍五岭用 50 万人,修建秦始皇陵和阿房宫达 70 余万人,加上其他劳役,役使
人数超过 200 多万。秦时全国人口约 2000 万左右,而服役的人数总计不下 300 万,占当
时全国总人口的 15%,仅修陵墓一项的花费就占到当时全国财力的 1 / 3。庞大的劳役造成
农业再生产难以维持,农民不堪重负。隋炀帝急功好利、急于求成,建大运河、修驰道、
筑长城以及三次东征高句丽等,动辄征调上百万民力,负担沉重,民怨沸腾。尽管其中的
相当数量的大型工程是有利于社会和长远的,但由于负担过重而引起农民反抗。在中国,
积极有为与人民负担是并行的。超越负担导致王朝覆亡,形成对积极政府的负面效应。
其次是官员腐败。积极政府的支柱是庞大的官僚行政机器。在帝国制度下,天下归一
家,官僚只是皇帝的 “家臣”。皇帝通过 “君子重义”的儒家文化的规范,用很低的正式
报酬让官僚为其办事。但是,官员考取功名而获取官职,需要支付大量成本,并有自家发
财以光宗耀祖的冲动。只是在常态下,这种冲动缺乏制度空间。而当君主积极有为,兴办
大量公共工程时,便为各级政府官员提供了自利空间。因为公共工程的具体操办人是各级
官员,由于缺乏复杂系统的预算和会计手续,更无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造成公共工程的
操办者有利可图。费正清因此认为,在传统帝国体制下, “政府作为有组织的 ‘贪污集
体’”,即缺乏约束官员的体制而造成官员的普遍的 “假公济私”行为。 而层层官僚的自
〔 15〕
利必然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甚至造成王朝的灭亡。
再次是消极民众。积极政府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多权力,民众成为政府行为的服从者。
政府与民众构成主人—奴役关系。为了保证政府的积极行为能够高效贯彻,必然压制民众
的不同意见。因此,政府愈是积极有为,民众愈是消极服从。社会活力由此受到抑制,甚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