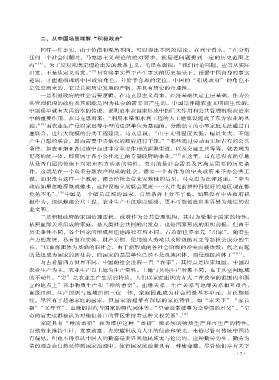Page 7 - 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P. 7
二、从中国场景理解 “积极政府”
同样一件事实,由于价值和视角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列宁看来,“在分析
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
内” 。为了反对从既定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
〔 6〕
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只有将事实置于产生事实的历史场景下,根据中国自身的事实
〔 7〕
逻辑,才能准确理解中国政府角色,并给予合理的定位。中国的 “积极政府”的角色不
是凭空而来的,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一是积极政府的社会需要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作为公
共管理机构的政府及其职能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是伴随农业文明而生长的。
中国很早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说明治水在国家形成中的巨大作用和公共管理机构在治水
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
础。” 而农业生产是以家庭等小型的组织单位为基础的。分散独立的小型家庭无法通过自
〔 8〕
愿联合,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马克思说:“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
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
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
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在这里,马克思没有简单地
〔 9〕
从是否自愿的价值上判定东西方治水的特性,突出的是社会需要及其满足需要的历史条
件。这就是在一个众多分散农户构成的社会,需要一个有作为的中央政府来举办公共工
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府,便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马克思为此评述道:“中央
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
荒芜不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自然条件十分不平衡。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积
〔 10〕
极作为,组织修建公共工程,农业生产不仅难以延续,更不可能创造出世界最为灿烂的农
业文明。
二是积极政府的家国治理逻辑。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其行为受制于国家的特性。
依照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出发点,也是国家形成的组织前提。但由于
历史条件不同,各个国家的形成和组建路径有所不同。古希腊世界率先 “出家”。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以及阶级的对立等新社会成分的生
长,“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
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 。
〔 11〕
与古希腊西方世界不同,中国的社会进程一直 “在家”,其特点是以家组国。中国以
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以土地为生产资料。土地与其他生产对象不同,在于其空间地域
的不动性。“定”是农业生产生活的特质。人们以家庭组织的方式 “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
立的地点上”从事物质生产和 “种的蕃衍”。血缘关系、生产关系与地缘关系相互重叠,
血缘组织、生产组织与地域组织三位一体,家庭因此成为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并长期延
续。尽管有了超越家庭的国家,但国家治理带有深厚的家庭特性。如 “家天下” “家长
制”“父母官”、血缘的世代与国家的朝代同体等。“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皇
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
〔 12〕
家庭具有 “种的蕃衍”和为维护这种 “蕃衍”而必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特性。
以勤劳来维持生计,发家致富、光宗耀祖成为人生的使命和荣光。韦伯尽管对传统中国持
有偏见,但也不得承认中国人的勤奋是世界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这种勤劳为生、勤劳为
荣的理念会自然延伸到国家治理中,使得国家统治者具有一种使命感。尽管他们享有天下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