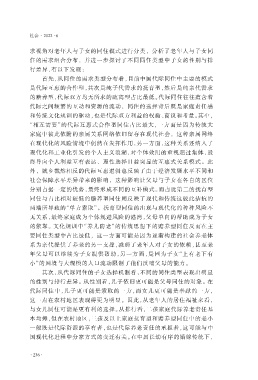Page 243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243
社会·2022·6
求视角对老年人与子女的同住模式进行分类, 分析了老年人与子女同
住的需求组合分布, 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同住类型中子女的性别与排
行差异,有以下发现:
首先,从同住的需求类型分布看,目前中国代际同住中主要的模式
是代际互惠的合作型,其次是纯子代需求的抚育型,然后是纯亲代需求
的赡养型,代际双方均无所求的疏离型占比最低。 代际同住往往蕴含着
代际之间频繁的互动和资源的流动, 同住的选择背后既是家庭责任感
和传统文化规训的驱动,也是代际双方利益的权衡、商议和考量。其中,
“相互需要”的代际互惠式合作型同住占比最大,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大
家庭中彼此依附的亲属关系网络依旧留存在现代社会, 这种亲属网络
在现代化的风险情境中仍然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关系还纳入了
现代化和工业化引发的个人主义浪潮,对个体效用的重视超过集体,最
终导向个人利益互有表达、 理性选择日益突显的互惠式关系模式。 此
外, 城乡截然相反的代际互惠逻辑也反映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
社会保障水平差异带来的影响, 这种影响让父母与子女在各自的区位
分别占据一定的优势,最终形成不同的互补模式。 而占比第二的抚育型
同住与占比相对较低的赡养型同住则反映了现代和传统这彼此拮抗的
两端所导致的“单方索取”。 抚育型同住的出现与现代化的种种风险不
无关系,最终家庭成为个体规避风险的港湾,父母单向的帮助成为子女
的依靠。 文化规训中“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下的赡养型同住反而在主
要同住类型中占比最低,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逐渐构建的社会养老体
系为亲代提供了养老的另一支撑,减弱了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甚至老
年父母可以继续为子女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子女“上有老下有
小”的困境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限制了他们反哺父母的能力。
其次,从代际同住的子女选择机制看,不同的同住类型表现出明显
的性别与排行差异。 从性别看,儿子依旧更可能是父母同住的对象。 在
代际同住中,儿子更可能是索取的一方,而女儿更可能是奉献的一方,
这一点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从老年人的居住福祉来看,
与女儿同住可能是更有利的选择。 从排行看,二孩家庭代际养老责任基
本均摊,但在农村地区,三孩及以上家庭抚育型和赡养型同住中的老小
一般既是代际资源的享有者,也是代际养老责任的承担者,这可能与中
国现代化进程中分家方式的变迁有关。 在中国长幼有序的婚嫁传统下,
· 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