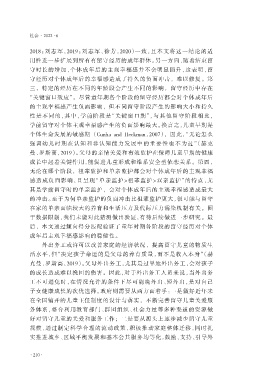Page 217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217
社会·2022·6
2018;刘志军,2019;刘志军、徐芳,2020)一致,且本文将这一结论的适
用性进一步扩展到所有有留守经历的成年群体。 另一方面,随着结束留
守时长的增加,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会明显回升,这表明,留
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幸福感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冲击, 难以修复。 第
三, 特定的经历在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留守经历中存在
“关键窗口效应”。 尽管童年期各个阶段的留守经历都会对个体成年后
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但不同留守阶段产生的影响大小和持久
性是不同的,其中,学前阶段是“关键窗口期”,与其他留守阶段相比,
学前留守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 换言之,儿童早期是
个体生命发展的敏感期 ( Cunha and Heckman,2007), 因此,“无论怎么
强调幼儿时期在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不为过”(赫克
曼、罗斯高,2019)。 父母的亲情关爱和有效监护在保障儿童早期的健康
成长中起着关键作用,能促进儿童形成和维系安全型依恋关系。 第四,
无论在哪个阶段, 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都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
感造成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尤
其是学前留守时的单亲监护, 会对个体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最大
的冲击。 至于为何单亲监护的负面冲击比祖辈监护更大,很可能与留守
在家的单亲面临较大的养育和生活压力及代际压力濡染机制有关。 囿
于数据限制,我们未能对此猜测做出验证,有待后续做进一步研究。 最
后, 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验证了童年时期各阶段的留守经历对个体
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
外出务工或许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提高留守儿童的物质生
活水平,但“决定孩子命运的是父母的养育质量,而不是收入本身”(赫
克曼、罗斯高,2019)。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过早地外出务工,会对孩子
的成长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因此,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当外出务
工不可避免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晚外出、短外出,是对自己
子女健康成长的次优选择。 政府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做好近年来
在全国铺开的儿童主任制度的设计与落实, 不断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体系,整合利用教育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等多种渠道的资源做
好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服务工作; 二是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留守儿童
规模,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流动政策,积极推动家庭整体迁移,同时扎
实推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鼓励、支持、引导外
· 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