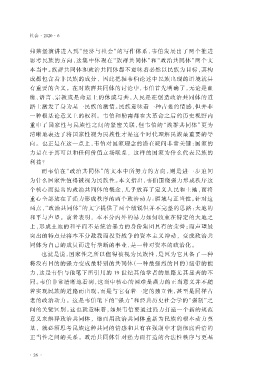Page 33 - 《社会》2020年第6期
P. 33
社会·2020·6
弗莱堡演讲进入到“经济与社会”的写作体系,韦伯发展出了两个推进
思考民族的方向,这集中体现在“族群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两个文
本当中。 族群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都不意味着必然以民族为目标,其构
成都包含着非民族的成分, 因此把握韦伯论述中民族出现的语境就具
有重要的含义。 在对族群共同体的讨论中,韦伯首先明确了,无论是血
缘、语言、宗教或是命运上的休戚与共,人民是在创造政治共同体的道
路上激发了身为某一民族的激情。 民族意味着一种古老的情感,但并非
一种根基论意义上的权利。 韦伯和勒南都在大革命之后的历史视野内
重申了国家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密关联,但韦伯的“族群共同体”更为
清晰地表达了将国家性视为民族性才是这个时代理解民族最重要的导
向。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韦伯对国家理念的潜在疑问非常关键:国家的
力量在于其可以和任何价值立场联系, 这样的国家为什么代表民族的
利益?
而韦伯在“政治共同体”的文本中所努力的方向,则是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国家性值得被视为民族性。 本文指出,韦伯围绕强力形成秩序这
个核心而提出的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几乎放弃了定义人民和土地,而将
重心全部放在了强力形成秩序的两个政治动力:疆域与正当性。 针对这
两点,“政治共同体”的文字提供了两个敏锐但并不完整的思路:大地的
和平与声望。 前者表明, 本不分内外的暴力如何收束在特定的大地之
上,形成土地的和平而不是统治暴力的身份集团具有的荣誉;而声望最
突出的特点是将本不分敌我而投资战争的资本主义冲动, 变成政治共
同体为自己的成员而进行垄断的事业,是一种对资本的政治化。
也就是说,国家性之所以值得被视为民族性,是因为它具备了一种
将没有目的的强力变成最特别的共同体(一种最强烈的目的)纽带的能
力,这是韦伯与他笔下所引用的 19 世纪其他学者的思路尤其显著的不
同。 韦伯非常清晰地看到,这当中核心的困难是强力的正当意义并不随
着实现民族的道路而出现,而是与它有着一定的独立性,甚至是同样古
老的政治动力。 这是韦伯笔下的“强力”和经典历史社会学的“强制”之
间的关键区别。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韦伯要通过强力打造一个新的规范
意义来解释政治共同体, 继而用政治共同体重新为民族的根本动力奠
基, 就必须思考民族这种共同的情感和只有在强制中才能彻底看清的
正当性之间的关系。 政治共同体针对强力而打造的合法性秩序与更基
·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