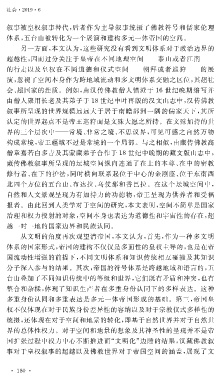Page 187 - 《社会》2019年第6期
P. 187
社会· 2019 · 6
叙事被皇权叙事替代,后者作为主导叙事统摄了佛教符号和儒家伦理
体系,五台山被转化为一个展演和建构多元一体帝国的空间。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这些研究没有看到文明体系对于政治边界的
超越性,因而过分关注于皇帝在不同地理空间———泰山或者江南———
的行走以及皇权在不同道德和仪式空间———朝拜或者巡狩———的展
演,忽视了空间本身作为跨地域流动和多文明体系交融之区位,其超社
会、超国家的性质。例如,由汉传佛教僧人镇澄于 16 世纪晚期编写并
由僧人聚用长老及其弟子于 18 世纪中叶再版的汉文山志中,汉传佛教
叙事所呈现的世界规模远远大于居于南瞻部洲一隅的儒家天下,其所
认定的世界起点不是帝王巡狩而是文殊大愿之所持。在文殊加持的世
界的三个层次中———常境、非常之境、不思议界,可见可感之自然万物
构成常境,帝王疆域不过是常境的一个局部。与之相似,由藏传佛教高
僧章嘉若白多吉及其蒙藏弟子合作于 18 世纪中晚期的藏文版山志中,
藏传佛教叙事所呈现的坛城空间纵向连通了在上的本尊、在中的密教
修行者、在下的护法,同时横向联系起位于中心的金刚座、位于东南西
北四个方位的五台山、布达拉、乌仗那和香巴拉。在这个坛城空间中,
自然和人文景观呈现为有加持力的功德物,帝王呈现为供养者和受福
报者。由此回到人类学对于空间的研究,本文表明,空间不简单是国家
治理和权力投射的对象,空间本身也表达为道德性和宇宙性的存在,超
越一时一地的国家边界和民族认同。
从文明的角度再次观望清帝国,本文认为,首先,作为一种多文明
体系的国家形式,帝国的建构不仅仅是多面性的皇权主导的,也是在帝
国流动性增强的前提下,不同文明体系和知识传统相互碰撞及其知识
分子深入参与的结果。其次,帝国的符号体系是跨越地域和语言的,五
台山叠加了不同知识传统中的等级和世界,它们既有矛盾和冲突,也有
整合和杂糅,体现了知识生产者在多重身份认同下的多样表达。这种
多重身份认同和多重表达是多元一体帝国形成的基础。第三,帝国皇
权不仅体现在对于民族身份差异性的容纳以及对于宗教仪式多样性的
统摄,还体现在对于空间和地景的转化,即基于自然世界并对于自然世
界的总体性权力。对于空间和地景的想象及其神圣性的呈现并不是帝
国扩张过程中权力中心不断推进而“文明化”边陲的结果,汉藏佛教叙
事对于皇权叙事的超越以及佛教世界对于帝国空间的涵盖,展现了文
· 1 8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