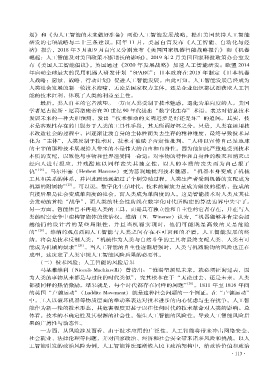Page 114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P. 114
划》和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两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提出美国扶持人工智能
研发的七项战略与二十三条建议。同年 11 月,美国白宫发布 《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
济》报告,2018 年 3 月和 9 月白宫又分别发布 《美国国家机器智能战略报告》和 《机器
崛起:人工智能及对美国政策不断增长的影响》,2019 年 2 月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发
布 《美国人工智能倡议》。英国通过 《 2020 年发展战略》加速人工智能研发;欧盟 2014
年启动全球最大的民用机器人研发计划 “ SPARC”;日本政府在 2015 年制定 《日本机器
人战略:愿景、战略、行动计划》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由此可知,人工智能发展已经成为
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一轮技术海啸,无论是国家权力主体,还是企业组织都试图获取人工智
能的技术红利,体现了人类的利益至上性。
最后,类人自主的它者欲望。一方面人类受制于技术魅惑,退化为单向度的人。美国
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 “数字化生存”术语,表达对信息技术
发展未来的一种大胆预测,发出 “技术推动的文明进步是好还是坏”的追问。其实,技
术是客观性存在的且服务于人类的工具性手段,其无所谓好坏之分。只是,人类在运用技
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因逐渐让渡自身的主体性而失去生存的精神维度,最终导致技术异
化为 “主体”,人类反制于技术时,技术才被赋予否定性批判。“人得以宣传自己是地球
的主宰的那种技术展现给人带来的不是伟大的自由和自身性,因为他如此严重地受到技术
本质的支配,以致他与事物和世界遭受同一命运:对事物的特性和自身性的毁灭和消灭已
经向人进行报应,并残酷地以同样丧失其独立性,以人的本质的丧失而为自己报了
仇” 。马尔库塞 ( Herbert Marcuse)更为悲观地批判技术魅惑,“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
〔 26〕
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过了个别劳动过程,人类生产者受到机器的支配成为
机器的附属物” 。可以说,数字化生存时代,技术的解放力量成为解放的桎梏,造成的
〔 27〕
直接后果是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而人类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是智能技术对人类及其社
会发动的首轮 “战争”,而人类的社会性防线在数字化时代所构建的算法边界中失守了。
另一方面,智能体已不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它者存在,并在与人
类的时空竞争中建构智能体的统治权。维纳 ( N. Winener)认为,“机器能够并肯定会超
越他们的设计者的某些局限性,并且当机器实现时,他们可能既是高效的又是危险
的” 。维纳的观点强调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工智能发展的终
〔 28〕
结,将会是技术反制人类,“机械作为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工具将最终支配人类、人类有可
能成为机械的奴隶” 。当人工智能的自主性逐渐增强时,人类与机器脱钩的风险也正在
〔 29〕
成型,这决定了人类审视人工智能风险后果的必要性。
(二)技术风险:人工智能的风险后果
马基雅维利 ( Niccolò Machiavelli)曾指出:“谁渴望预见未来,就必须征询过去,因
为人类的事物从来都是与过往的时代类似”,究其根本在于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人类
都被同样的热情激励。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1811 年至 1816 年间
〔 30〕
的英国 “卢德运动”( Luddite Movement)就是这种社会问题的一个例证。在 “卢德运动”
中,工人以破坏机器等物质层面的举动来表达对技术进步的内心忧虑与生存抗争。人工智
能作为新一轮的技术形态,其危害程度更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技术革命对人类的影响。总
体看,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根源的社会性,催生人工智能的风险性,导致人工智能风险后
果的广博性与动态性。
一方面,从风险涉及面看,由于技术应用的广泛性,人工智能将带来冲击网络安全、
社会就业、法律伦理等问题,并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以人
工智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为例,人工智能算法逐渐嵌入民主政治架构中,给政治价值和政治
1 · ·
1 3